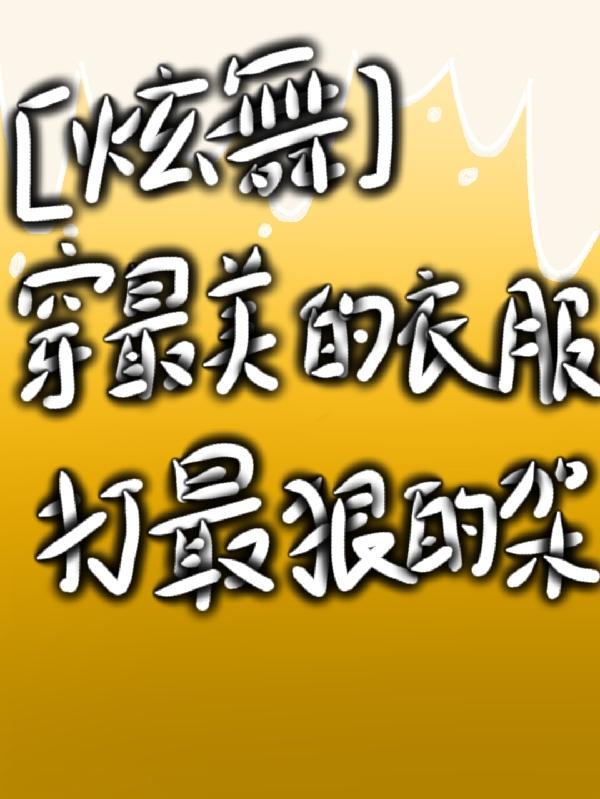爱上中文>死亡飞行视频 > 第十一章神秘的米勒先生(第3页)
第十一章神秘的米勒先生(第3页)
显然,我把她只敢想象的事用语言表达了出来。
然后,她的拳头松开了,目光迷茫起来,她把一只手举到唇边,轻轻用指尖触碰着嘴唇,当她开口说话时,她那轻快的语速迟缓下来,似乎每一个字都要突破拦在嘴边的手指的阻挡。
“是的,”
她说“想一想后来那些将军们频频来访,这事的确不同寻常,你看,我听伯瑞兹先生说过,军队会他是怎么说来着?‘协助’只是其中一个意思,我想那些话是‘赞助她的事业’,这句话的意思是?”
“意思是伯瑞兹提供政府基金支持她重新开始环球飞行。”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我能告诉你这件事,我是第一次未遂起飞时掌管帐目的人,所以我知道钱应该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这一次,即第二次,情况全然不同——根本没有帐单寄来,不论是飞机花费,还是维修费,不论是机库租用费,还是燃料费,什么都没有。”
我皱起眉头“艾米莉意识到这一切了吗?”
“是的她非常忧郁,与她前次飞行截然相反,当初她飞到火奴鲁鲁时,她热情万丈,心情愉快,笑个不停。”
阿美一直说她飞行是为了“其中的乐趣”
我问:“你问过她军方为什么对这次飞行如此热衷了吗?”
“问过,似乎是可我并没有往那方面想,我更担心的是她身边的一些朋友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拒之门外,都是一些她信赖的人。”
“她怎么说?”
“她对我说,‘我们不可能总做我们想做的事’。”
从一个毕生都是我行我素的女人嘴里讲出这句话,的确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谁被‘拒之门外’,玛戈?显然,你一直保有这份工作。”
“哦,例子太多了,奥克兰有一个男孩原本一直在她的保护之下——好像是叫鲍比麦尔斯?我知道她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但我听到普图南先生对她说,那个男孩是一个粗俗下流的偷窥狂,于是让他走路了。”
“什么样的男孩?多大年纪?”
“十三、四岁吧?他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原打算监听这次飞行的。还有一个叫麦克门美的男人,他自己建立了一套无线电操作网络,准备帮助普图南先生接发飞行进展情况,也被扫地出门了。”
“谁?你是说那个男孩?”
“两个都是。”
我伸手向后,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我一直把它同钱包放在一起。我拧开钢笔的笔帽“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沃特麦克门美,住在洛杉矾,是无线电方面的专家,有时为门兹先生工作。”
我记下这些情况“那个孩子的名字?”
“鲍比麦尔斯。”
寄居在一所受到总统青睐、将军们频频来访的房子里,这个女孩一直过着受荫庇的生活。
她继续说:“那个名单非常长,内森,助手、顾问、志愿者,统统像垃圾一样被扔出去了,”
一道若有所思的神情在她的眼内一闪“还有阿尔伯特布莱斯尼克,一名摄影师。”
“拼一下他的名字。”
她拼出他的名字,我把它写下来,她解释说:“普图南先生亲自挑选他,给ae做‘正式摄影师’。他非常年轻,大约二十二岁,很有才华,他至少应该陪她飞行一段旅程的。”
有意思,普图南与报界做交易,他们从阿美用电报或电话发送回家中的飞行日志中节选摘录,然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一名随同飞行的摄影师可以获得许多独家照片。
“这名摄影师,布莱斯尼克,在第一次试飞期间就准备同行了吗?”
“不,我猜普图南先生是在四、五月间才找上的他。阿尔伯特本来已经做好同行的准备了,直到ae起飞的前几天,当米勒先生发现阿尔伯特也要参与飞行时,他大为恼火,我听到他对普图南先生大喊大叫。”
“于是,阿尔伯特就忽然成为不受欢迎的一员了。”
“是的内特,还有一些事我要告诉你,是私人事情,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说吧。”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在我们两个人还未来得及答话时,乔——那名男仆——探头进来,说:“狄卡瑞小姐——普图南先生与米勒先生回来了。”
“但他们现在不应该回来!”
“普图南先生回来了,米勒先生同他在一起。”
然后乔关上门,离开了。
“天啊,”
她说“在明天下午之前他是不应该回来”
“我们无处藏身,”
我说“我也不打算从窗口跳出去。”
我同她走到起居室,在那里,普图南——仍像往常一样穿着双排扣灰毛料西服,打着黑白相间的领带——正一边走进来,一边说:“你想让我怎么做,米勒?沉浸在公众的悲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