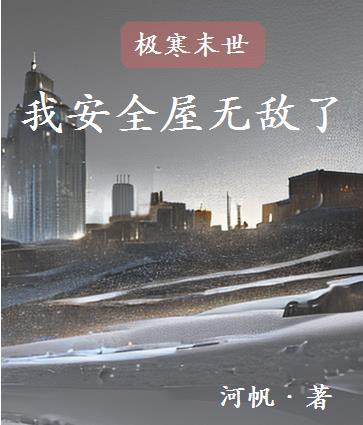爱上中文>春庭月的意思是什么 > 第117章 求得终(第3页)
第117章 求得终(第3页)
幼幼完全傻了,压根不知道容欢抽的什么疯,再这样下去,肋骨都快被他勒断了,她开始扭晃身子,喉咙里不断挤出呜呜声,容欢方有所觉,缓缓撒开手。
幼幼捂着胸口呼呼喘气,待眼儿一晙,气急败坏地拍他一下:“你干什么呀,害得我差点憋死了。”
容欢却一阵嘿嘿傻笑,攥住那小手,吻着她的每根手指头:“我的好宝贝,你终于醒了。”
幼幼被他吓出一身鸡皮疙瘩,怎么一觉醒来,他就跟转了性似的,变得那么肉麻?
他又用下颌摩挲着她的手背,幼幼觉得分外扎手,仔细一瞧,才现他整张脸似乎清减一圈,下巴成锥,颧骨偏高,眼皮底下一痕青影,脸上更是多出一层胡茬。
幼幼惊呼:“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
“很难看吗?”
容欢颇为无辜地摸摸自己的脸。
幼幼当然不知道,在她昏睡这段期间,瑜亲王可是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照拂,连镜子都没照过。
她点点头:“难看!”
一向注意仪表的瑜亲王,大概一辈子都没被人说过丑,可如今他毫不在意,只是紧紧揽着她,唯恐她会跑掉一样:“只要你安然无恙就好……幼幼,我求你了……今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好不好……”
容欢嗓音中藏着疲倦与痛楚,觉得自己已经被她折磨到老了二十岁。
幼幼偎在他怀里,呆呆眨了眨眼,反应过来:“我睡了有多久?”
他回答:“十天了……”
“十天?”
这么久!记得上次撞树她也没有昏迷这么久啊。
“你一直在烧。”
回忆当时情景,容欢脸色有点惨白,又赶紧搂了搂她。
其实幼幼根本没有打算自杀,只不过恨他不相信自己,一时冲动所为,现在想想,也是心有余悸,她抿着小嘴不吭声。
容欢低头问:“好宝贝……你还生我的气呢?”
他不提还好,一提幼幼就忍不住委屈:“反正你也不信我,不如让我死掉算了!”
容欢就跟吞了金块似的,脸庞十分抽搐难看,然而当她挣脱开他,又跟没了骨心主一般,忙扑上前拥住,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幼幼,你原谅我,是我错了。”
他仿佛小鸡啄米一样,轻轻啄着她颈上的肌肤。
幼幼难忍心内酸涩,吸了吸鼻子,一字一顿地道:“我、我就是想要告诉你,当年我可以为孟瑾成做的事,现在也同样可以为你做。”
“我知道了……”
容欢眼底蓄满伤楚,缓缓掩下睫,“幼幼,我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我努力了那么久,你都不肯看我一眼,如今你回来,我总是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害怕你什么时候又念起孟瑾成的好,害怕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就又破灭了,既是如此,那还不如……”
幼幼方知他心底的真正想法,情不自禁泪流满面:“那你现在肯信我了吗?”
“信了……真的信了……”
容欢近乎虔诚地吻了下她的额心。
“那、那你还会不会再把我轰出书房,不理睬我了?”
幼幼撅着小嘴,对于某人先前的所作所为,心里可仍在记仇呢。
“不会。”
此际她睫毛水漉漉的,似那淋了雨的蝴蝶,可爱到不行,容欢低头轻轻呷了一下,“今后你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还差不多……幼幼稍稍消了一点气,忽一转念,又委屈十足地质问:“那我绣的荷包呢,当时我绣了好久的,你居然就那么给扔出窗外了!”
“你瞧……”
容欢从袖里掏出一枚粉物——可不就是她绣的双莲并蒂锦绣荷包么,“其实那晚你跑掉之后,我就给捡回来了。”
幼幼一瞧还真是,而且干干净净,没有半点土污,转而又问:“那我绣得袜子呢。”
“穿着呢。”
容欢笑了笑,“还有鞋垫子,很是合脚。”
幼幼瞟见他腰上系的腰带也是自己绣的那条,不自觉微微红了脸。
容欢则跟牛皮糖似的捱着她,凑在耳畔轻轻呵气,话音中满是讨好的意味:“那你写得极好,我现在都会吹了,想不想听?”
幼幼心房像打翻了蜜罐一样甜,却又不肯端下劲儿,拂着自己一绺小头嘟囔:“不要,反正人家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她这一声“人家”
叫的,既似撒娇撒痴,又似衔恨抱怨,且软软哝哝,有气无力,纵使百炼钢金刚也是化为了绕指柔。
“怎么会不重要?”
容欢听得浑身骨酥筋软,魂都生生销了三分,赶紧嘬了一口她的脸蛋,“你是我的心尖肉,眼珠子,最最重要的心肝宝贝。”
要知道瑜亲王说起肉麻话来,也是当仁不让的。
幼幼隐忍不笑,那一股子甜意几乎要从眼底溢了出来:“就这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