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质子配婢女 > 第102章(第1页)
第102章(第1页)
说完他便显露出几分赧然,担心她又与他玩笑,起身就要出去,嘴里还念叨着:“睡这么久,你定是饿了吧,我去看看……”
她笑着看他颇为慌不择路的身影,怎么会有这样心思单纯,什么都写在脸上,还这么容易害羞的人?
沈渊刚迈出两步,眼前阵阵发黑,身形摇摇晃晃的。
她吓了一跳,赶紧起身扶住他:“你怎么了?”
“我……”
他还没说出来,便栽倒在她怀里。
她吓了一跳,轻呼:“沈渊!醒醒!”
沈铎听到这声惊呼,赶紧闯了进来:“阿渊怎么了?”
见此情形,他赶紧扶沈渊躺下,探他的脉搏,又叫京墨拿了药箱过来。
段曦宁忙问:“他怎么了?”
沈铎道:“伤到了头,应是瘀血未散,服了药便好。”
闻此,她这才几不可闻地松了口气。
似是担心沈渊,沈铎一直在床边守着,没有出去的意思。
段曦宁的视线饶有兴味地在他和沈渊之间逡巡,猛然想到以前看到的一些野史秘闻,眸中打量愈浓。
以前想不通的一些事,忽然便能想通了。
好一会儿,她突然听到一句:“女皇陛下。”
段曦宁先是一愣,冷笑:“沈先生好眼力。”
“阿渊一向克己复礼,又是质子,轻易出不得云京。突然与女子出现在此,除了女皇陛下,在下想不到旁人。”
沈铎缓缓道,“大概没人能想到,大桓的女皇陛下,会纡尊降贵亲临深山之中。”
段曦宁仍旧带着一如往常浅笑,说出的话却堪称尖刻:“旁人也想不到,天下士人皆崇敬的竟陵先生,会躲在深山中做缩头乌龟,连亲骨肉都不敢认。”
沈铎脸色倏然沉了下来,眸色幽深,透着薄怒:“女皇陛下,慎言。”
“几句实话不敢听吗?”
段曦宁冷哼,话语愈发不客气,“他在梁宫人人可欺,难听的话不知有多少。你一句刺耳的都听不得,他可听了十几年。”
“怎么会……”
沈铎愕然,难以置信,“阿鸿从未与我说过。”
段曦宁愈加不留情面地讥讽:“呵,沈鸿若与你说了,你还会乖乖为他所用吗?指望别人给你养儿子,你可真有本事!”
沈铎依旧不愿相信,反驳:“那可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天家无父子,又哪里会有兄弟?何况还是异父兄弟。”
段曦宁冷嗤,“朕以为,只有沈渊年纪小见的世面少,才会如此天真,竟没想到先生一把年纪亦是如此。这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沈铎恼怒之下反唇相讥:“女皇陛下不惮以恶意揣测旁人,那您呢?不也是对阿渊极尽利用吗?”
段曦宁不屑地一笑:“论利用,朕与先生相较,甘拜下风。若是他知道,自己是……”
“莫要叫他知道!”
沈铎急急忙忙开口打断,眼中是难以掩饰的慌乱,“莫叫他知道,他受不了的。”
段曦宁冷眼扫过:“沈先生既没这个心,就接着与他做陌路人,别自作多情。”
她不愿他知道自己不堪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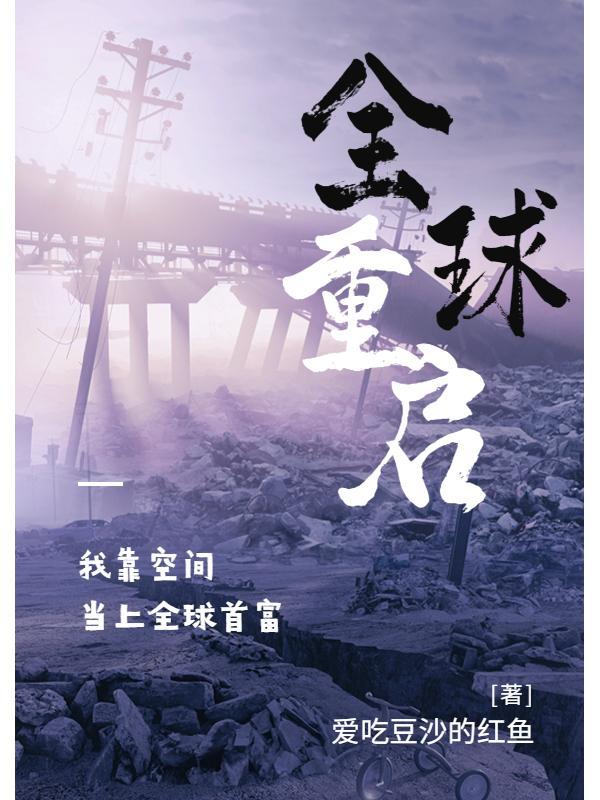
![被迷恋的劣质品[快穿]](/img/1403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