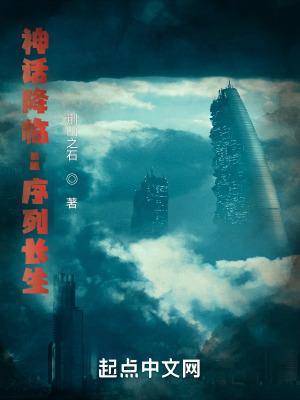爱上中文>他对小河说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史彬见他眼波流转,不知道他正想着些乌七八糟,问到:“我近日也听说扶菊先生词曲曼妙清丽,别具一格,颇得坊间青睐,从前竟不知文柳兄还有此等才华?”
刘柳忙摇头道:“其实不是我谱的,借用我家乡一个人的曲子混口饭吃。”
史彬道:“青楼卖曲总不是光彩之事,你既缺盘缠,为何不制卖香皂呢?”
刘柳:“方子不是抵给你了麽…”
史彬哼道:“我可曾说过不準你再做香皂生意?为何同我这般见外?你借用他人之曲糊口,怎不见你有丝毫避忌?难道你同他比同我还近熟?这人是谁?以前怎未听你提过?”
刘柳头大:“当然不全因为方子,桂娘怀孕生産,不宜再劳累,我做香皂的手艺又不好,即便做了恐怕也卖不出去,因此才想到卖曲子。”
史彬如闻惊雷:“你和杨桂娘有孩子了?几时成的亲?”
刘柳有点心虚,含糊道:“我本是杨家赘婿,成不成亲都差不多,差不多…”
史彬:“无媒无聘,也未拜天地高堂?”
刘柳突然感受到了广大男同胞们面对丈母娘灵魂拷问时的压力,仿佛一个打算裸婚的穷鬼突然被问到“房子买了吗?钻戒几克拉?”
,不由得冷汗直流,说:“要麽补一个?”
史彬笑道:“再说吧。走,去你家认个门,这几日收拾收拾,同我回临安。”
刘柳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别扭,可能是因为太听话了,史彬一句话而已,自己就带着一家子远赴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临安是自己来到这个年代后一直向往的地方,似乎也没有可拒绝的理由。刘柳稀裏糊涂地爬上史彬的马车,史彬见他乖顺,心气略平,回身对一名属下说:“去查,将他这段日子见的人、经的事,一一查仔细了。”
二人携手下车,刘柳叫开院门,将老冯、冯山、吉朵儿一一介绍给史彬认识。史彬问到:“这一大家子都是你一个人养着?”
刘柳心说哪裏哪裏,都是周董养着,我只是替他做慈善的,嘴上含糊应了一声,又嘱咐吉朵儿端茶不要烫到手。史彬见他忙前忙后,毫无家主风範,暗暗摇头,道:“文柳兄还是这麽平易近人,到临安后为兄安排些人手助你打理内宅如何?”
老冯插话道:“你要去临安?怎麽不和家裏商量一声?”
刘柳:“这不是刚要商量吗…”
史彬皱眉道:“文柳兄身为一家之主,此等事务还做不得主吗?”
刘柳:“也不是…”
老冯又插话道:“次山在建康府好容易闯出些名气,就这麽全扔下了?”
刘柳:“您老不也说过卖曲子不是正道,叫我找个正经事做吗?”
史彬说:“正是,我既找到文柳兄,自不会教他再为生计发愁。”
二十三、错付
晚间桂娘哄睡了依依,同刘柳閑话道:“如今你同史彬久别重逢,他又邀你同去临安,也总算可以安定些了吧,怎麽你反倒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刘柳说:“你看出来了?”
桂娘笑道:“眉毛快拧成八字了,我便是瞎了也看得见啊。”
刘柳索性披衣坐起,道:“我总觉得怪怪的。这麽说吧,就好比你大学毕业了,没找着工作,去投奔一个混得还不错的同学,如果他说‘来吧,我帮你找个工作’,就满正常;可是他说‘来吧,别在外头瞎混了,我养你’,就不怎麽正常了吧?”
桂娘摇头道:“史彬喜欢你,你难道还没看出来?”
刘柳几乎跳起来:“可是我是男的啊!不对,我不是男的啊!你是说他喜欢男的?不对,不管他喜欢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是啊!不对,乱了乱了…”
桂娘按住他,道:“你冷静点,我只问你,你喜欢他吗?”
刘柳定了定神,说:“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根本毫无可能的问题。如果他喜欢的是男的,最后发现我不是,岂不是要怪我欺诈?”
桂娘说:“如果你喜欢他,何妨坦诚相告,也许他能接受原本的你呢?”
刘柳连忙摆手道:“那更糟糕!即便他能接受我是女的,难道还能接受我继续假扮男子在外行走吗?”
桂娘叹道:“这麽多年,你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改回女子身份,安定下来,难道不好吗?”
刘柳摇头:“绝对不可能,这个年代女子生存何其艰难!仰人鼻息怎比一切由我来得自在!我这就去辞了史彬,不去临安了,我带着你们在建康,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桂娘忙拉住他:“大晚上的瞎跑什麽!再者说,你本来一直想去临安,若是因为史彬在,反而不去了,又是什麽道理?你若不想与他有牵扯,只需明白算账就是了,与你人在何处又有什麽关系?这岂非着相了。难道你带着一家子在临安,就不能好好生活了?”
刘柳:“…好像也对。”
桂娘推他道:“快睡吧,明日还有的忙呢。”
刘柳一夜辗转反侧,次日顶着熊猫眼,哈欠连连的去同徐妈妈告辞。徐妈妈还以为那几个爱嚼舌根的得罪了刘柳,不住向刘柳道歉。刘柳哭笑不得,只好将原委同徐妈妈讲了一遍。徐妈妈心知挽留无用,只好祝他“鹏程万裏”
等等,又叫来刘柳平日相熟的几个歌妓为他设宴饯行。
衆人虽然时常在背后编排刘柳取乐,但听说他要走,都十分不舍。且不说摘星阁衆歌妓因刘柳一夜翻红,只他平日既无架子,又待人有礼,从不占便宜吃豆腐,就足够赢得衆人好感了。巧荧在席间甚至红了眼圈儿,道:“不菊,不是,扶菊先生,您真的非走不可吗?您这麽好的人,可惜巧荧不能伴随左右,只能祝您早日康複,同夫人开枝散叶,将来百子千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