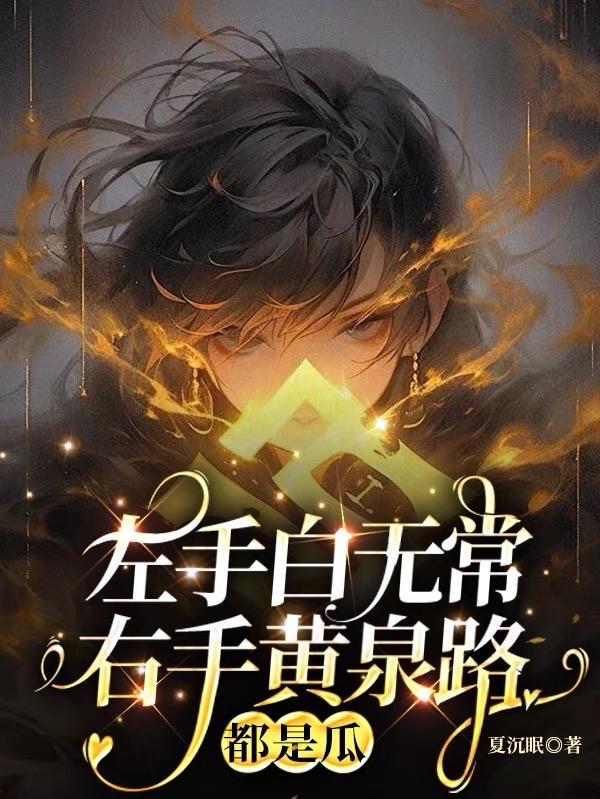爱上中文>农历三月十七日 > 第67章(第1页)
第67章(第1页)
那点血腥味在他唇齿间扩散开,变得更加明显。花涧抿了抿唇,抿到的不只有血腥,还有像是草木汁液的苦涩,铡得他唇角和脸一起痛起来。可是那种痛又逐渐变成冷,从口鼻开始,一股一股顺着鼻道和喉咙道往下灌,继而盘踞到右上腹,硬邦邦坠着。他很轻地吸了口同样冰冷的空气,冷然分辨着混杂在耳鸣声中的窃窃私语,直到它们最终化为一声女人尖利的哭叫,刺向他的喉咙。
花涧巍然不动。
他冷静而割裂地观望着那些过去,好似被抽离了感知,觉不出疼也觉不出冷。直到一点温热触碰到他的眼角,再捋过鬓发,花涧才终于从过往上移开目光。
“过去了吗?”
沈亭文温声问。
“过去了。”
花涧说。
沈亭文展开手臂,轻缓而坚定地再次将他抱进怀中,隔着薄薄的衣衫描摹过嶙峋的脊骨。
“从这里往南走二十里,”
花涧说,“过一座桥,有个叫南井的村子,我出生在那里。”
花涧闭上眼,一切便随着他的思维展开,纤毫毕现。女人半长的头发散乱,一边哭叫一边把他往木门里塞。他跟着女人一起哭,扒着门,扒得指甲都裂出来血,又隔着漏风的门缝听见叫骂。女人身后站着的已经不是人了,风吹烛火,把那东西的四肢拉长又催折,头部扭曲成看不懂的色块,丑陋得像是扒在网上的蜘蛛。直到他哭得再哭不出声,屋外的声音才终于停下。
女人打开门钻进来,瘫靠在背后破烂的柜子上,在黑暗中不住地给他擦脸,嘴里念着含糊的字句。
……她说什么来的。
花涧能想起来,她说,要是死了就好了。
那是他关于人生最初的记忆,但这段记忆很快断了,断在他尚未愈合的指甲里。
因为女人死了,喝药死的。
后来花涧回忆过很多次,怎么都拼凑不起一个完整的人。他不记得女人的名字,不记得女人的脸,只记住了消不下去的青紫和那只扭曲的怪物。短命鬼和扫把星绊住了他的脚,他摔在石砖下,压倒簇红的鸡冠花,血便和花混在一起。于是他也想,要是死了就好了。
可他没有死成。
他明明不记得女人喝药后挣扎的样子,却本能地走向不同的路。他被覆着薄冰的河面欺骗,也被死亡欺骗。污浊的河水要了他半条命,错误的用药要了他另外半条命。
可他终究没死成。
那只怪物的器官在他身体里跳动,隔着一条疤和薄薄的肌肉脂肪。怪物要他活着,因为怪物没了婆娘,不能再没有儿子。它比他们要更怕死,怕到将镰足转向生养他的女人,怕到趿拉着鞋,一刻不停守在窗户都要靠报纸补的破学校外,怕到在开学前夕烧了他想方设法跟人求来的课本。
他站在愈发破旧的木门外,盯着糊满了油污的黑墙。雨珠子砸下来,砸在水洼里,砸湿他的脚腕,像走不完的湿淋淋的道路。
花涧在窗边站定,灯光落在飘窗台上,被他捉到手里。他说:“我在十三岁那年第一次来到县城,没有期待,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那是他第一次反抗,借着一条他人搭起的路,从一个囚笼走进另一个囚笼。他挤在人群里,被人群淹没。他格格不入,又成为他们合群的代表。青少年间的等级规则比成年人更加赤裸残忍,他们不会伪装也不屑于伪装。混乱糟糕的家庭情况、瘦弱多病的身体、沉默敏感的性格、陈旧磨损的书笔,乃至卓然出群的成绩,都能够成为他与众人不合的理由。
何况欺凌并不需要理由。
困住他的东西变成了沾着笔水的衣服,故意被踩掉的鞋,揉皱的试卷,掩着鼻子的窃窃私语,无足轻重,重若千钧。怪物也不再在意他了,它有了新的女人,有了新的儿子。他变成了短命鬼下的催命鬼,该死的活不长还要吃要喝的秧子。他走在其间,能握住的只有错页的书和翻不开的本子,好似握着仅存的救命稻草。
但他活着,他小时候没有死成,这辈子就得活下去,他得想办法自己活下去。
“人生是一条不回头的路。”
花涧转身,仰眸看见了沈亭文的脸,他站在他身后,将将好的距离,一抬手就能把人抱进怀里。花涧后腰抵着台沿,他撑住了,说:“……四中距离襄阳高中不到八百米,连我在内,走进去的只有三个。”
花涧后来看到一个说法,说教育本身是筛选分流的过程。这句话放在他身上或许没有错,在此之后,他没有再见过任何在初中三年出现在他身边的人。纵然再有针对,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也少了太多。
命运的齿轮好似终于洗了锈,迟缓而恰好地转动起来。花涧走在其上,被它在某个残阳正好的傍晚送到老师身边。那一天,他侧身对着晚阳,将手里的书放进书架,听见老人问他是否可以帮个忙。
他被太明亮的残阳灼了眼,额上沁出薄薄的汗。手指随之收紧,感受到书封上凹陷的印痕。老人从他身侧走过,拂开绕着他的灰尘。他伸出手,就这样简单地用一个忙换到了进入画室的机会,换到了老人对他的优待,也第一次真正见识到认知之外的世界。
他学着执笔,学着看清自己,也学着自处,在笔墨之间划过三年匆匆时光,收到梧大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时间就这样流逝下去,或许能够写给花涧的是最好的结果,但世间永远写着一个故事中不会写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