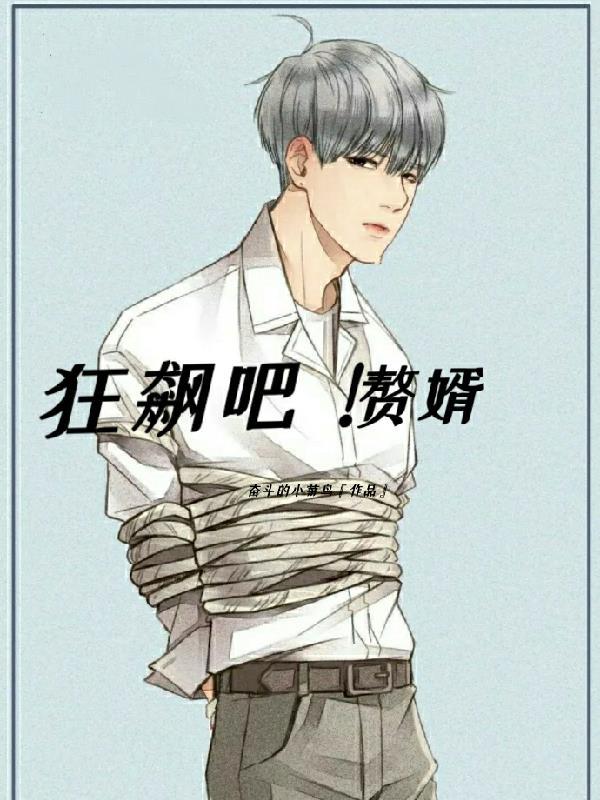爱上中文>掠妻讲什么 > 第101章(第1页)
第101章(第1页)
镇北王妃忙带着嘉和跪下,自行请罪。
其实她知道文帝正是器重镇北王的时候,为了不伤能臣的心,文帝都不会重罚嘉和,但理是这样的理,场面还是要做一下,该递的台子还是要递过去的,这样文帝才能顺台阶重拿轻放。
反正也不是头回了,这样的人情往来,镇北王妃熟得很。
文帝还没说话,荀引鹤却先开了口,他道:“陛下实不相瞒,臣赶到王府时,见到卿卿不堪受辱跳了湖,气得神志不清,恨不得能以牙还牙给她出气,还是卿卿安抚住臣,说镇北王如今正率兵剿匪,日后大召的北境也还有赖王爷守护,不能伤了王爷的心,更不能坏了文臣武将之情谊,唯有将相和,大召才能兴。”
镇北王妃心一沉,其实事情最后怎么收尾,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江寄月作为一个受害者说这样的话,会显得她格外识大体,能在文帝心里留个极好的印象,镇北王府这边更是白捡了个人情让她做。
这江寄月很聪明,又或者说是荀引鹤很聪明,他在为江寄月铺路。
文帝听了果然问道:“她当真这样说?”
荀引鹤道:“陛下有所不知,卿卿在香积山时,江先生不以男女为论,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她也爱看书,常常手不释卷,有时候臣与她辩书,还要被她辩倒。”
文帝笑了:“难怪你会喜欢她,能把你辩倒,她确实有些本事。”
看着皇后,“朕都说了是般配的,皇后如今可信了。”
皇后只能赔笑。
文帝道:“那叔衡你来说该怎么罚,嘉和此事确实做得过分了,原是她要强占人夫,如今不仅欺负到范廉娘子头上去,还要拖无辜的江寄月下水,这不好好罚一罚,朕也没法跟自己的其他臣子交待啊。”
他的言下之意是,皇帝可不只有一个臣子的心要照拂,镇北王的名头也总有不好使的那天。
镇北王妃已经笑不出来了。
荀引鹤道:“既然卿卿都说了话,我自也要有些觉悟,才配得上她的格局。可郡主也不是头回这般欺辱人了,再不加以管教,恐酿大祸。不如这样吧,让郡主去道观里住一年,修身养性,改改这脾气。”
镇北王妃还没来得及欣喜,嘉和便嚷道:“我才不要去道观里,那里又冷清又没趣,规矩又多,去那儿与坐牢守活寡有什么区别?”
文帝道:“是你做错了事去受罚,不是让你去享福的,别住一年了,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什么时候再回来!”
镇北王妃可不敢让她乱说话了,忙压着嘉和谢恩。
她低头的那刹那,荀引鹤的眼神阴冷下去,目光悠悠在嘉和身上逡巡了一圈,然后若有似无地移转开。
只是去道观修行一年怎么够?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说是送去反省,结果给道观捐了好些符纸钱,于是那些贵女不过是换了地方继续享乐。
但荀引鹤仍然选择送嘉和去道观,一来是为了帮江寄月做人情,二来自然是因为道观偏僻,好出事。
嘉和能一口一个骂江寄月娼妇,骂得毫无负担,足见没有教养,指不定来前镇北王妃怎样编排过江寄月,她才学得这样快。
既然如此,那他帮她们把名头坐实了,届时看看究竟谁才是丑闻满上京的娼妇。
出了宫,还要回府应付荀老太爷,其实要迎娶江寄月这件事上,最难过的还是孝道。
荀引鹤登马车时,侍弩便告知:“皇后娘娘已命人出宫送信了。”
荀引鹤沉了沉深思,侍弩正要退下时,便听他勾了唇,漫不经心的笑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嘲讽:“你说等我回去后,会不会有家???法等着我?”
侍弩一惊,正要回答,荀引鹤已经登车掀帘进去了,侍弩这才意识到,荀引鹤要的不是个回答,而只是一句讥讽罢了。
世家总是如此,即使荀引鹤如今贵为万人之上,但只要他还是谁的儿子,那父亲便可名正言顺的用孝道与家规压制他。
好似他天生就该是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必须规规矩矩地待在那四方的盒子里,略有越界就是不敬不孝,该被削足切肢。
说来印象中,荀引鹤也是头回如此明目张胆地忤逆父亲,因此当荀老太爷请出家法时,把荀家上下都惊动了,只是在荀引鹤踏入宗祠之前,荀老太爷发了大火又把他们赶了出去。
因此,荀引鹤只看到手持家法的仆从,白发丛生的荀老太爷,以及那些如山般堆叠排列的牌位。
荀老太爷未及他见礼,便喝道:“跪下!”
荀引鹤一顿,从容下跪。
荀老太爷喝道:“给我家法伺候这逆子!”
那两个仆从听命,左右分站着,一人抱举着粗重的木棍朝荀引鹤打下去,砸打的声音又重又闷,只一下,就让荀引鹤疼出冷汗,闷哼了声。
原本到此时,后落棍的人都会停一下,观察一下法号者的神色,判断这场处罚是否要继续下去,但今天格外特殊,刑罚的两人一下接着一下,手里并未有任何的停顿。
荀引鹤似乎听到了幽怨的哭声,大约是荀老太太也在,只是无论是他用手掌绑着毛笔学写字,还是眼下他被责打,荀老太太都说服不了掌控力极强的大家长荀老太爷。
而如今,他最得意的儿子要挣脱出他的掌控,他又焉能不气,不惊,而这样的惊怒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日渐年迈,日渐松弛的权力掌控之上。
荀老太爷害怕着有一天他还活着,他的孩子却当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要请出家法,即使这个儿子是他最满意的儿子,即使这个儿子已经贵为丞相,他也要用家法好好地训诫一番,以此来显示他还没有老,更没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