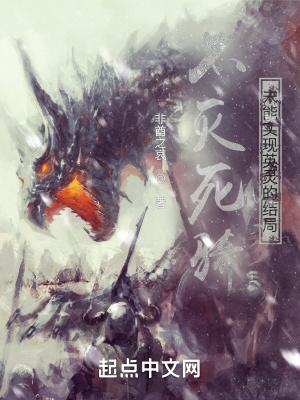爱上中文>乡村野和尙 > 第41章 寡妇门前是非有点多(第1页)
第41章 寡妇门前是非有点多(第1页)
“没,没什么。。。那什么,我爹最近腰不舒服,想弄点野蜂蜜吃,说好的让张麻子去,刚才他惹恼了我,我不想让他去了。”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赖二毛连忙找了个理由,准备搪塞过去。
糊弄人都不会。
腰不舒服喝蜂蜜,就是兽医也不敢开这方子啊。
秦兽哪里会信他的鬼话,厉声喝道,“少扯淡,再不说实话,嘴给你撕成牛欢喜。”
眼瞅着瞒不过去了,赖二毛和张麻子对视了一眼,两人你推我,我推你,都支支吾吾不敢开口。
刚才还狗咬狗,斗得不可开交。
面对秦兽的逼问,两人却突然有了默契,又站在了同一战线上,选择用沉默保守秘密。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一丘之貉同时缄默,让秦兽突然感觉到,事情或许真不简单。
得想个法子,撬开赖二毛的嘴。
软的不行,还必须来硬的。
秦兽早就注意到赖长贵不在家,要不然以他的性格,早就出来叨叨个没完了。
他去了哪里,秦兽自然也是知道的。
不如就从赖长贵这里下手。
秦兽嘴角突然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计上心来。
“你要是不说,我现在就去王寡妇家找赖长贵,我倒要让靠山屯的村民,都知道知道咱们的好村长,腰都累伤了,整天夜以继日地到底在忙些什么,操得什么心。”
王寡妇水性杨花,风流成性,过门不几天,就将自己原本就体弱多病的丈夫,伺候脱相死在了床上。
寡妇门前是非多,王寡妇总是给人一种唯恐事儿不多的感觉。
自此再也没人能约束她的天性了,每日流连于牌桌酒局,勾结一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无赖。
加上正是三十左右的年纪,就像熟透了的樱桃和水蜜桃,都开始往下滴水了。
只要王寡妇打男人窝里走过,这些男人的婆娘准会跟自己男人吵架。
就连柳疙瘩这样的,一有几个钱就往王寡妇家跑,去填补她那深不见底的寂寞和空虚。
村长赖长贵更是王寡妇的座上宾,这家伙只要一有空,就去慰问孤寡妇女,不是挑水浇田,就是深耕犁地,干得那是满头大汗,热火朝天。
有时候柳疙瘩省吃俭用攒几个钱,猴急猴急地往王寡妇家里跑,在门外就听见屋里比母猫叫得都揪心,继而就传来一个粗鄙的男低音,“你这小骚货,太扛造了,这十来分钟,我都冲刺八回了,我都快累吐了,你就饶了我吧。”
这声音他当然熟悉,是赖长贵这个老杂毛的。
畜生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来了八回,也不考虑王寡妇能受得了吗。
这老杂毛只知道自己泄兽欲,一点也不心疼王寡妇。
哪像自己,每次顶多几秒钟,免得王寡妇遭罪。
自此柳疙瘩就将村长这个情敌,视为眼中刺,肉中钉。
他借高利贷原本是想翻本,捞一笔大钱,带着王寡妇远走高飞。
怎奈人算不如天算,他是逢赌必输,不多久就花光了借款,从此身无分文,王寡妇再也没让他进过家门半步。
他最多就是趴在窗下,听听自己的女人与赖长贵耳鬓厮磨,过一过耳瘾。
声音还是熟悉的声音,女人还是那个女人,但每当情到深处,嘴里喊的却不再是他柳疙瘩的名字。
这种心碎的声音,使他学会了酗酒,每到想起王寡妇就让自己喝得烂醉,用酒来麻醉自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