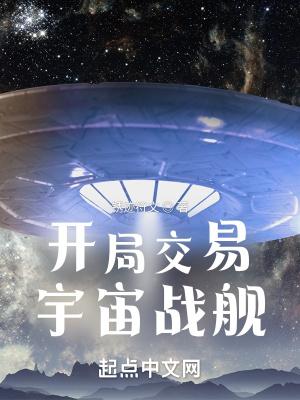爱上中文>明月台赋全文免费阅读TXT > 第29章(第3页)
第29章(第3页)
-
那少年原名江吟,一年前被人贩子骗到晟都来卖进了云水居。据他所言,当年同行的还有十来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在大漠里病死了几个,剩下的有的被辱弄至死,有的还如他一样苟活在无边黑暗之中。
先前还有个比他小些的,半夜翻墙出逃被抓回来,先是在众人面前挨了一顿鞭刑,后来又被强按到辣椒水里,生生疼死了。
我听他说得残忍,心里一算,一年前正是沈澜为了整修军队而大肆募役的时候。再往前问,几乎每一次渊人南迁,都逢上了天灾人祸。他们过得太苦,便听信谣言,被人送到这“纸醉金迷”
的万明来,成了供人消遣的玩物。
江吟说,这些人的足迹,远至万明以南,近至……樊城。
难怪那时在樊城的酒楼中,小厮多番暗示许多“新鲜玩意儿”
。我只以为是万明风味的吃食,没想到竟是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等到今日回宫,我必得给沈澜修书一封,让他多加关注民生、整顿官吏。好好的百姓,不能再受这样的糟蹋了。
我爽快地给了他银两去赎身,那瘦麻秆似的龟公虽很不乐意,但碍于我上那枚银蛇扣,还是不情不愿地放了人。
“这银蛇扣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出了云水居,与江吟并肩走在路上。
“晟都最大的钱庄挂的是蛇纹旗,据说除了宫里的贵人,所有人的银钱都经过银蛇庄主的手。庄主的心腹助手,都有一枚这样的银蛇扣。”
江吟人很机灵,点到即止,没有过多追问我这银蛇扣的来路。
这是伽萨随手送给我的,十有八九他就是那个阅钱无数的庄主,掌控着晟都半数银钱的人。
有了这个小东西,即便是我在晟都撒泼耍赖,他们也得敬着我。
“听说晟都有个兽台,在何处?”
我又问。
“在西南边。”
江吟飞快地答。
他实在心细,这一年来将晟都大大小小的事物都了然于胸。凭着这些,他将来或许对我有大用。
我不再多问,只嘱咐他在晟都找个生计做,若将来有飞鸽传书,务必及时回应。江吟点头应允,我便挥手让他离去。
夏去秋来,农忙时节将至,兽台也该筑起来了。
猛兽嘶吼声里,我捏着袖角随意找了个看台。饿虎徘徊在中央铁笼高筑的圆场中,不时妄图扑向四周的看客,又被守卫用长枪吓退。
血红的兽睛游走在诸多看客身上,我紧张地屏住气息,仿佛回到了夜宴场上。伽萨一刀贯穿虎的头颅,救我于虎口之下。
可惜眼下这个奴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众人一阵喝彩,那个懦弱的奴隶便被推入圆场。他两股战战,顺着大腿淌下一股骚腥的水来,随即仰天哀嚎一声,大有拼死一搏的架势。然而天不遂人愿,看客的起哄声还未止,他便已被虎撕咬去了半个肩膀,紧接着就是颅骨碎裂声。
那个奴隶连声呜呼也没来得及出,就成了一缕血溅兽台的亡魂。
何等惊心动魄的一幕,却日日在这兽台中上演。伽萨若真呆在这里,更是不知历经了多少次生死一线的时刻。我如今见到的他,是浴血而成的。
我蓦地觉,他这个人所经历的残酷之事,远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血腥味弥散升腾,我身上亦如同着火般热起来。这是情动之兆,我心道一声不好,急忙想从人堆里挤出去,却见那虎吃完了人,此刻眼睛正攥在我身上。
我一迈步,那虎便逐步逼近了,刹那间凌空跃起扑在我面前的铁栏上,出如雷的震响。它着魔似的撕咬着铁栏,厚重利爪几乎要将精铁压弯。身侧的看客贵人皆含畏地退开两步,将我全然暴露在虎的眼中。
“推他下去!”
僵持之间,不知谁突然出声喊道。顷刻,周遭人的眼神从畏惧转变为了狂热。
他们一哄而上钳制住我的手脚,高举过铁栏。
下一刻,天旋地转,我滚落圆场。
庸民依旧在欢呼吵嚷。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本就不期盼一场厮杀,而是期待着虎将我撕成碎片、血流成河。
晟都生活穷奢极欲,享尽酒池肉林之后,能让他们叫嚣激动的也唯有流血和死人。
方才我尚且在为那虎口亡魂叹惋,焉知眼下我亦深陷樊笼,命悬一线。
虎大吼一声,振得我两耳嗡鸣不止,一股腥甜涌上喉头,鲜血几乎是喷洒而出。那血滴落地面,仿佛触了虎的软肋,叫它一改先前凶残之相,先是趋近地面嗅了嗅,又踯躅几个来回,这才重又目露凶光,蓄势待。
![入殓师[无限]](/img/1006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