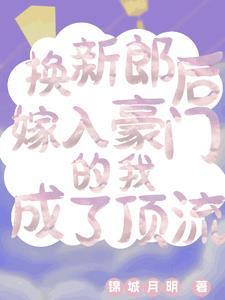爱上中文>离亭宴带歇的歇指什么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那时她宫内还有个贴身侍奉的嬷嬷,姓什么她都不记得,寿眉被她支走了,嬷嬷见白日里殿门紧闭,推门而入。
她只知道自己当时在萧翊的怀里睡着了,不知萧翊在做什么,嬷嬷猛地发出大叫,吓醒了她,他们像受惊的鸟儿离开彼此,对视一眼,仅需一眼,交换了所有的罪恶。
那个嬷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宫中,凭空消失一般。
她偶尔会在午夜梦回之时想起这号人、这桩事,想她到底有何结局,想萧翊到底做了何事,直到天亮都不能合眼。
碧珀合香花晒干,旃檀粉末与麝伴,一缕青丝绕红线,藏尽痴念,这是萧翊的香囊,她岂会不知。
惨绿的旧事(6)
萧清规一昏迷就是半日,陷在陈年的美梦与罪孽里无法自拔,恍惚间她深知周遭发生的一切,听到寿眉等宫人的呼唤声,萧旭一路将她抱回嘉宁宫,贺兰云裳又将那些厌恶的锐器扎进她的皮肤内。
她早已变得千疮百孔,也曾生出过绝念,只是牵挂着一人,才牢牢攥着一丝生机不放。
她听到寿眉提议,要请贺兰世镜前来,坦诚说她一直以来回避与贺兰世镜相见,其实是因为她害怕贺兰世镜,她拚命晃动着身躯表达抗拒,贺兰云裳似乎听懂了。
只听贺兰云裳说道:“长公主怕是自己不愿醒,如此,便叫长公主多睡上片刻。”
寿眉低声不知说了什么,她只听清了“王爷”
二字,萧翊,萧翊,她再不醒来,萧翊就要出征北朔了,她一定要阻止,他绝不能去北朔。
萧清规用力撑开疲惫的双眼,猛然坐起身来,感觉到浑身黏腻的湿汗,有些劫后余生之感。
贺兰云裳与寿眉同时叫道:“长公主!”
她扯开被子爬下床去,不顾寿眉的阻止走到门口推开殿门,寒冷的冬风迎面袭来,令她打了个哆嗦,汗水瞬间干涸了一般,双目也愈发清明。
寿眉赶紧将门关严,贺兰云裳也上前劝阻:“长公主刚醒,还是回床上安歇……”
“兄长呢?”
“长公主,王爷还在京中,只不过怕是没在宫内。”
寿眉最知眼下说什么话能让她定心,不断安抚着,“王爷好好的,北朔皇室生了些变故罢了,侵扰了寒州疆域……”
“更衣,本宫要去见皇上。”
“长公主……”
萧清规迳自去取衣袍,举止慌乱,寿眉与贺兰云裳对视了一眼,见她无奈点头,才上前接过衣物服侍萧清规更衣。
步辇穿行于夤夜的御街,萧清规险些摔了下去,匆匆闯进议事堂,众人已散,唯有萧旭独坐在桌案前,疲惫地揉着脑袋,肩背略有些佝偻。
看到萧清规的瞬间萧旭连忙挺直了脊背,起身迎了上来,关切着:“皇姐可是刚醒?如何自己过来了,派人传唤一声,朕过去便是……”
萧清规紧紧握住他的手,问道:“北朔发生了何事?”
萧旭答道:“北朔皇室似乎生了内乱,三皇子万俟格打着自立的旗号率十五万大军出逃,突然进攻寒沙川,守将抵挡不及,皇兄说,戚将军怕是最多能坚持五日。”
“你要派兄长亲征?”
“并非朕的指派,是皇兄自己请旨要……”
“断然不可!”
萧清规严厉拒绝道。
萧旭满眼不解:“皇姐为何反对?眼下再没有比皇兄更合适的人选,况且皇兄一向……”
“我说不可就是不可。他从西骊回来尚不到半年,你就忍心这么快又将他派到北朔苦寒之地?北朔铁骑骁勇善战,颇为熟悉天险关隘,当年父皇派去多少精兵良将,悉数折在了三尺雪原,他是我的兄长,也是你的皇兄,你怎么忍心派他前去?我朝难道就再无其他将才不成?孙恕孙将军宝刀未老,齐昌平也正值壮年,还有去年刚平过岭南匪寇的少将军魏路……”
她对朝中众臣如数家珍,一股脑说出好些人选,萧旭则愈发不解:“皇姐?你这是怎么了?西骊内部割据,七王乱政,皇兄远征西骊可谓速捷,也并未受什么伤,皇兄自己都未当回事。至于昔年折损的将帅,如今已经过去近三十年,我朝兵力岂可同日而语?皇姐提及的这些人选,朕未尝没与皇兄商议过,孙将军的腿疾一遇阴湿天气便会疼痛难忍,断然无法前去北朔,齐将军乃东夷旧臣,效忠我大誉不到两年,朕断不可能将二十万大军交到他的手里……”
她知道,她怎么会不清楚,没有人会比萧翊更合适,但萧翊就是不可。
萧旭仿佛下定裁决般告诉她:“皇兄已领了虎符,大军最迟后日便会开拔,皇兄的前锋部队已经连夜出发。”
“他何时领的虎符?”
“皇兄刚走不久,群臣也不过片刻前散去的……”
萧清规遽然转身看向寿眉,眼中挂着明显的仓皇:“他可来看过我?”
寿眉咬唇摇头,萧翊确实没有来过。
萧清规顿时红了眼眶,忽然想起什么,同萧旭说:“阿旭,他真的不能去北朔,你定然知道,他的生母是北朔女子,你这是让他朝着自己的亲族挥戈,有违人道……”
“皇姐这是何话?”
萧旭愈发不明白了,她今日举止实在是反常,说的话看似有理,实则不堪一击,不像她往日严谨的作风,“皇兄与我们都是父皇的子女,萧誉后裔,不管他的生母是北朔女子还是西骊女子,他都是我大誉的男儿,誉朝才是他的亲族,皇姐此话委实不该。”
萧清规几次张口,终是说不出口,殿外突然传来太监的通传声,萧太后已经走了进来,看样子听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