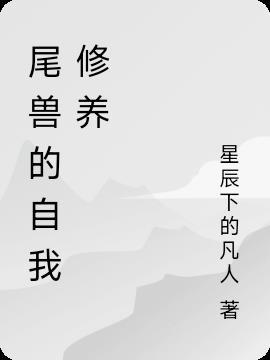爱上中文>扶鸾是什么意思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前两个月户部实在捉襟见肘,圣上没了法子,于是挪用内库给国库,宫中也因此缩减开支,相当于是圣上省了自己的用度给朝廷,此事百官称赞,都说君主贤德,但不看账的人不会知道,宫里这几年的开支极大,内库根本所剩无几,哪有那么多钱给户部。内库出纳又由内侍省掌管,纪芳要说他不清楚,那真是把人当傻子糊弄了。
短短一刹那,纪芳的呼吸乱了好几下,但到底是侍奉皇帝的人,这时还能保持镇定,赔笑道:“公主,历来国君都有自己的私库,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是啊,私房钱么,谁没有。”
程慕宁眉眼结了冰,“但朝廷穷得叮当响,圣上的私库还能掏出这么一笔,好了不得,三年前我可没见过这笔钱,看来我走之后,圣上是走财运了,别不是我挡了他的财运吧?”
她最后那句似笑非笑,语气凉到极致,纪芳扑通一下跪了地,他是最擅长审时度势的人,“公、公主……”
程慕宁看着他,“我再问你一次,到底哪儿来的?”
纪芳抽泣着把头重重磕在地上,那一下沉重响亮,仿佛一记重锤,把程慕宁那一点残存的希冀砸了个稀碎。她藏在袖中的手不住颤抖,转过身去,没有眨眼,眼泪已然掉在地上。
“所以,武德侯到底往宫里送了多少?”
她的声音很轻,语气平静到几乎没有波动,似乎也不是真的想知道这个答案,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
【??作者有话说】
看到有评论疑惑这笔私房钱的由来,可能是前文没有直说过,所以这章结尾补一下。
天高云淡,晴空万里。
许敬卿得了传召进宫,由小太监引着到达凝露台。此处是由宫里一座废弃的瞭望台改造而来,因此视野开阔,从东北方看过去,能看到整个政事堂四周,过去孝仪皇后就喜欢站在这里等先帝处理政务。此时许敬卿看到那笔直纤瘦的背影有片刻愣神,太像了,就连回过头时脖颈昂起的弧度,都如出一辙得让人厌烦。
程慕宁将鱼食递给侍女,噙着笑说:“舅父来了。”
“公主金安。”
许敬卿朝她浅行过礼,“不知公主传臣进宫所为何事?”
石台上已经摆好了茶具和棋盘,程慕宁道:“我回京许久,想与舅父叙旧,今日只你我舅甥二人,舅父不必讲究,请坐吧。”
许敬卿斜眼看台面,没有挪动步子。
程慕宁笑了一下,落座斟茶。那茶水从壶嘴流入杯中,抛出一条顺滑的斜线,茶香四溢。程慕宁推杯过去,“从前舅父常与父皇对弈,我那时年幼在旁观局,却也只窥得些皮毛,不知今日可有这个荣幸,得舅父赐教一二?”
“公主自谦了,那臣便恭敬不如从命。”
许敬卿这才坐下,很有气定神闲的姿态,“听说公主昨日去看过武德侯,不知侯爷这案子可有进展?”
他明知故问,程慕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小姜大人办事让人放心,只是我现观局势不明,许多事难以定夺,还需舅父指点。”
她话说得谦逊,许敬卿抿了口茶,说:“公主既称臣一声舅父,臣便没有藏私的道理。”
“如此,我就先谢过舅父了。”
程慕宁一手握着茶盏,面露难色,道:“户部日日游说地方借粮,可他们也仅愿意卖粮给朝廷,我瞧着国库那一堆烂账实在焦头烂额,不知该如何是好。”
许敬卿指间夹了枚白子,道:“公主既已扣了武德侯,想必心中早有决断,我虽与侯爷有姻亲关系,却也不敢在这种事上偏私,若侯爷能解朝廷危急,也是他功德一件,公主大可放手去做。”
“可事情难就难在了用人上。”
程慕宁看他落子,说:“侯爷能在姚州建造私库,说明他有绝对安全且熟悉的运输路线,原本此事让他来办是最好,但如今他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一时半会儿也无法了结,且他眼下的身子骨,只怕也扛不住长途跋涉。我考虑再三,他的长子何进林在工部任员外郎,品阶不高,平日也不起眼,由他出面更为合适。只是我从未见过这何大公子,听说他是婉儿妹妹的夫君?”
她口中的婉儿妹妹正是许家五娘许婉,程慕宁叫的亲昵,可实则与她并不相熟,约莫在宴上见过两面,印象里年纪还小,是个不爱说话的。
许敬卿点头道:“是,进林这孩子为人老实办事周到,公主若想用他,倒是选对了人。”
他看着棋盘说:“只是如今侯府一团乱麻,随时都有灭顶之灾,进林前几日来过我府上,战战兢兢说要辞官回家等结果,脑袋别在裤腰上,只怕办不了差事。”
说话间棋盘上已密密麻麻,程慕宁应对吃力,再三斟酌才落了一子,“这事他若办成,也算立了一功,无论武德侯的案子最后怎么定论,我都可保他不死,绝不让他受他父亲波及。”
许敬卿轻而易举地堵住了她的路,“可公主也知道,空口白话定不了人心。”
程慕宁顺着他的话问,“那舅父觉得该当如何?”
两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商量得有模有样。
许敬卿已经提前结束了这局棋,两手搁在大腿上,看着程慕宁说:“武德侯素来谨慎,唯恐一朝有变,银票成了废纸,故而把银票都换成了黄金,黄金运输需要人手,禁军中步军司指挥使的位置不是还空着,公主若有心用人,不若就让进林顶上这空缺,他也好调派人手。”
终于说到要紧处了。
程慕宁捏着黑子没有说话,不是先落子的人就能拥有主动权,这局她从一开始就失了先机,许敬卿棋高一着,逼得她无路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