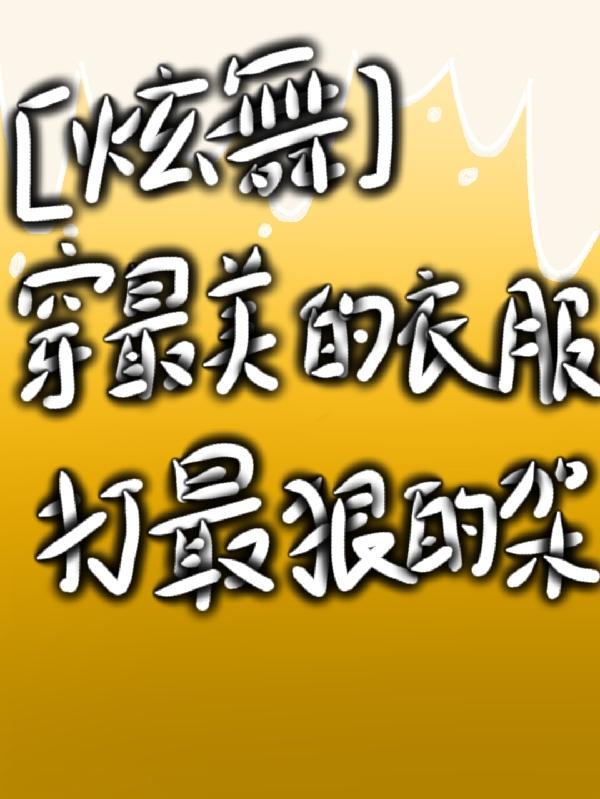爱上中文>媵妾知春(双重生)作者观渔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三叔家中就这么一个女儿,宝贝的像眼珠子一样,从没受过半点儿委屈,被惯的不成样子。可今日若真是因为她的一时意气毁了自己一生,而他又不曾出言劝阻,若是三叔知道了,难道还有他好果子吃?
他一心为着魏琅嬅,可魏琅嬅却恍若未闻,大有一种今日不把盛知春踩死便不收手的架势。
“好!魏姑娘果然直爽!”
此刻盛知春微微笑着,半边脸隐在暗处,瞧着令人心惊。
她站的端正,朝着不远处漆黑的角落唤道:“朱雀,如今外面乱哄哄的,都是因为你没有看顾好东西,且出来同诸位大人解释一番,也好叫魏四姑娘放心!”
“是!”
里面那人应了一声,缓缓从角落里走出来,身后似乎还站了几个人,但也都隐在黑暗处,让人看不清。
荣华似乎弯唇笑了一下,看着朱雀道:“你且说说,为何没有看顾好本郡主送给你家姑娘的贺礼?”
朱雀似乎是笑了一下,忙不迭地解释着:“郡主这是说的哪里话,郡主送来的东西咱们定然是要好生保管的,更何况这是我家姑娘交代的事情,又怎么会有不尽心的呢!”
她抬手招过身后几人:“郡主且看,珊瑚这不是正在这里!”
朱雀身后的几个小厮抬着荣华带来的那只箱子,箱子被人打开,露出里面红灿灿的珊瑚来。
见珊瑚完好无损,魏琅嬅霎时愣在原地,浑身的血凉了半截。
“怎么会,怎么可能!”
她大声尖叫着,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地上明明有红色碎屑,珊瑚竟然半点都未损坏。
见她如此形容,盛知春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魏四姑娘,先前我就同你说过,珊瑚并未损坏,你却是不听,口口声声要置我于死地,如今看到原物,又该如何说?”
嘲瑰抚掌笑道:“妙啊,既然珊瑚未碎,那地上的又是什么东西?”
“是朱砂。”
盛知春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众人探头瞧去,那人竟是方才还在疯疯癫癫地虞小娘。她此刻神志颇为清明,面上虽有疲态,却早没了方才跪坐在地上把玩碎屑的痴样。
她站起身来,先是朝着盛瓴和方大娘子行礼,随后声音虚弱地道:“主君主母,奴方才吃过药头脑不甚清醒,瞧见家中走水,便想着去救火,谁知忙乱中竟将供奉的朱砂佛像撞翻在地。地上那些碎屑正是碎掉的朱砂。”
说罢,她再次转头看向魏琅嬅,将盛知春护在身后:“奴不知魏家姑娘因何如此针对我家春儿,只是贺礼从未被毁掉,还请郡主明鉴!”
荣华点了点头:“娘子放心,我从未认定六妹妹毁了贺礼,自然不会怪罪于她!”
虞小娘垂下眸来,再次同郡主行礼:“妇人深谢郡主。”
此时事态明朗,众人皆清楚是魏琅嬅故意针对,皆在背后指点着她,议论起来。
“一早就听说这魏家的四姑娘同盛六姑娘不对付,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你可别说,人家当日为了顾侯爷,险些将盛六姑娘推下澄湖淹死呢!”
“什么?!这魏家姑娘竟然如此善妒恶毒?”
“可不是吗!她让郡主赶出了侯府,谁知竟在外面传扬是盛家姑娘伙同郡主将她赶了出去。这样的女人,究竟哪家敢娶!”
“嗐!人家自己都说了,今后可不用嫁人了,便是剃了头发要去山上的庙里做姑子呢!”
“那魏大人岂不会被气个半死!”
听着众人如此讥讽,魏琅嬅终于忍耐不住,破口大骂道:“你这贱人!定是一早便定下了计谋,专门等着我上钩!还有你这贱人小娘,伙同你一起害我,简直该死!”
“放肆!”
一旁的魏昭闭了闭眼,厉声喝道,“是谁教你的规矩,竟敢当众不尊长辈!还不快点跪下!”
“昭哥哥!你竟然帮着外人不帮我?!”
魏琅嬅不敢置信地盯着魏昭看,“我父亲待你如何?今日你如此对我,难道就不怕我父亲责罚?”
这话一出,众人皆看向魏昭,眼神中带了几分打量。
盛知春也同样望着他,心头微微发颤。
她先前曾听过些许传闻,说是魏昭自幼时失怙,由母亲抚育长大,可长到十岁上下,母亲又因病亡故,便辗转来到渝州城中,由族中三叔光禄寺卿魏泰初抚养,同魏琅嬅也算是青梅竹马。
魏琅嬅处处针对她,许是因为魏昭对她青眼有加,引来了魏琅嬅的嫉妒。
她本以为魏昭人品端方且能官至此位,在家中定是备受关照,可如今听魏琅嬅话中的意思,似乎他也是寄人篱下,有苦不能言。
思及此处,盛知春看向魏昭时,眼神中带了丝怜惜,仿佛在他身上瞧见了自己。
魏昭闭了闭眼,知道自己劝不动魏琅嬅,只好闭了嘴,不再发一言。
见魏昭不再理会自己,魏琅嬅嘴角抽了抽,正要开口责骂,却被荣华打断。
只见荣华抬手招过身侧侍卫,形容略懒散地吩咐着:“魏四姑娘方才说若是地上那东西并非珊瑚,她便剃了头发去做姑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四姑娘必是不能食言的。”
她站得端庄,朝前微微探着身子:“魏家今日只来了小魏大人和魏姑娘两人,怕是没什么人手送魏姑娘去山上,那我姑且派人护送吧!”
“是!”
侍卫上前一步,正要将魏琅嬅架起来,却听魏琅嬅嘶声怒吼挣扎着:“你敢!我父亲是光禄寺卿,朝中重臣,你竟敢如此对我!”
“哦!”
荣华似乎想起来什么,继续吩咐,“再派一些人去魏大人府上,好生同他说说魏姑娘的事,让他若有什么异议,便去寻舅舅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