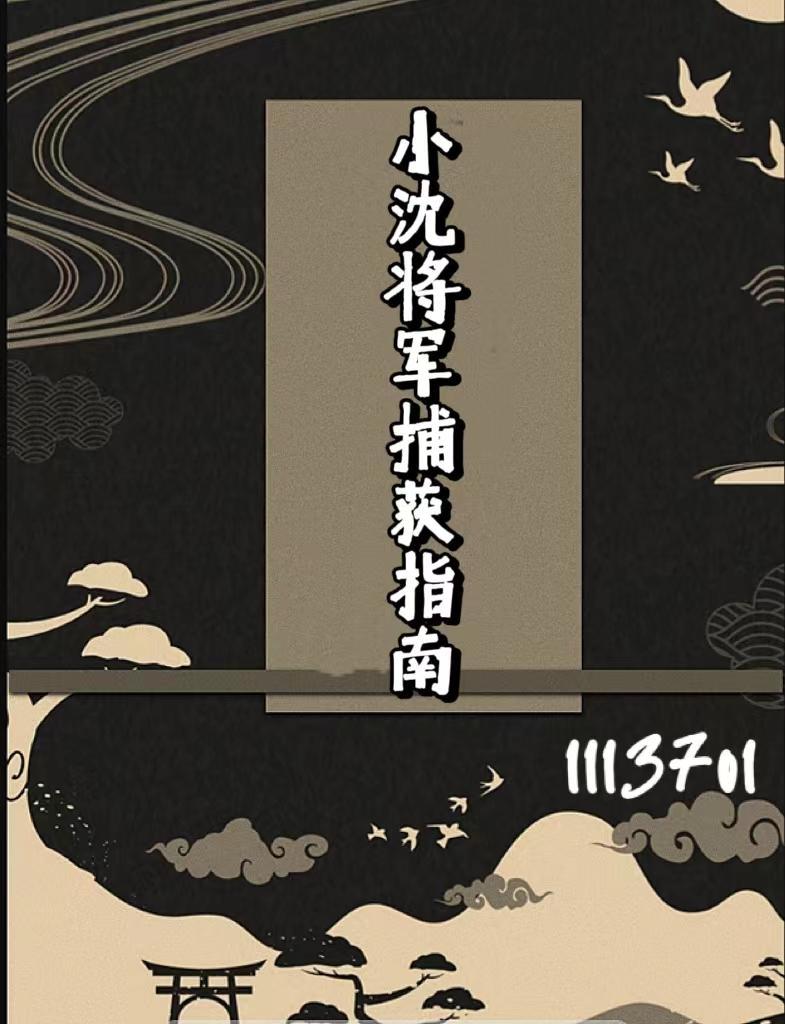爱上中文>铁血残明完结了嘛 > 第五百三十一章 贵宾(第2页)
第五百三十一章 贵宾(第2页)
庞雨见识过阮大铖的资产之后,对这帮阉党的土豪程度一点不惊奇,阮大铖在南京当掮客就已经那么有钱,冯铨在宫中的关系根深蒂固,京官中要想跟二十四衙门勾连的,很多最终都求到了冯铨门下,比阮大铖的单价和业务量又高了数倍不止。
“庞将军万勿谦逊,东虏凶残暴虐,数月前某往真定府拜祭卢总督,沿途所见荼毒之惨,实不忍闻也,首恶便是入边奴酋岳托,听闻将军将其阵斩,不禁夙夜难眠,今日某要代万千受难百姓,谢过将军的高义。”
冯铨严肃的向庞雨一揖,庞雨连忙避开,两人互相把马屁拍完,再客气一番之后,才各自分主客落座。
刚才冯铨有意无意的提到了卢象升,庞雨等那文士上了茶后对冯铨道,“先生方才提及,还曾去真定拜祭卢都堂,晚生曾与都堂大人在滁州并肩迎战流寇,虽只是一面,却如多年至交,未曾想一别便是天人相隔。”
冯铨叹口气,扭头朝着窗外看了一眼,“当日是他的幕友许德士在涿州病发,因之前某带领绅民捐助军粮时相识,便投靠到某府中,方得知建斗殉国,停灵于真定府,某便即刻赶去拜祭,其时遗体放于府城东关,真定巡抚、巡按皆在,却都说不认得是不是建斗,因不认定身份,一直无法收殓……”
(注1)
说到此处时,冯铨摇摇头停口不语,按照他说的时间,大概是十二月二十多的样子,清军全军东进横扫山东,庞雨正被围困在铜城驿,兵部焦头烂额,皇帝则对卢象升满腔怒火,朝中定然是没人愿意理会这件事,张其平和巡按对朝中怎么给卢象升定性没有把握,迟迟不认定卢象升战死,以免引火烧身,遗体也就无法收殓。
在通州呆了这些时间,兵部差官在各营查问历次作战功过,庞雨也得知一些消息,对当时的形势有了全盘的了解,知道卢象升的处境,但真听到冯铨这个亲历者说起,仍感觉有点悲凉。
“之后某又去了高阳,拜祭孙阁部,要说起来,某刚入翰林院时,便跟孙阁部相识了,未想最后一面是这般。”
冯铨语气萧索,庞雨从去年进入山东之后,经过的地区大多都是被清军蹂躏过的,见过的惨状又远比冯铨多了,最近在通州碰到的士绅,都有亲友死于寇难,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颓丧气息。
这短短两段话,庞雨对冯铨的印象立刻就立体起来,似乎冯铨是一个颇有信义且很念旧,他不知是否冯铨营造的形象,而且并不显得很刻意。
“此番两位总督和孙阁部此等众臣殉国,直隶百姓罹难者更是数不胜数,京城中几乎家家都有亲友在其中,宫中更是如此。”
庞雨听到此处,知道冯铨转入了正题,连忙打起精神,对冯铨关切的道,“各位老公肩负重责,又不能离京寻访亲友,当时担惊受怕又无能为力,现下收到消息,心情可以想见。”
冯铨叹口气,“流寇复叛于湖广,整个中原地方又不安宁了,原本说京师还是上善之地,但建奴多番肆虐,城中的老公多半来自河间、保定、真定各处,这次破了五十多城,北边到处都不安稳,各位老公忧心的,多年来薄有积蓄的,也想要有个安稳去处。”
“晚生这里已有预备,此前跟老先生提及大江银庄,本应年初在京师开张,但建奴一来到处都乱套,不是合适时候,但各位老公既有此担忧,五月定然开张。”
“庞将军现下可能定下利钱了?”
“存银的利钱一律都是五分,凡通过老先生来存银的,一万两以上三年取的银票,每万两给老先生二百两的心意,五年的三百两,要现银还是银票都听先生的。”
冯铨认真的听着,神色十分平静,对庞雨说的数字没特别的反应,实际上庞雨提到的是一大笔钱,他直观上觉得冯铨比阮大铖还有钱。
“之前南京那边有人说,可是给到过一钱五分,为何到了京师便成了五分?”
“南京的银子,是南京存南京取,京官的银子则是担忧北边不安稳,都是京师存外地取,在下要担着途中丢失的风险,部署相应的人马护送,船也要用自家的,这些都是成本。”
庞雨停顿一下又道,“除了利钱之外,晚生的银庄还有一个好处,凡存银一万以上的,我们都提供贵宾服务。”
冯铨愕然道,“什么贵宾服务?”
“对存银一万以上的贵宾,一旦京师有变,晚生的银庄将在天津为他们预备南下的船只座位,存银五万以上的,在下负责将他们由京师送到天津登船,走海路到江南上岸,并安排他们安稳立足。”
庞雨看着冯铨道,“存银十万以上的贵宾,他们的亲友也由晚生的属下接应,若是在保定、真定、河间、大名的,无论陆路还是海路,晚生的属下会负责将他们护送到江南,并保他们在江南地方取到银子立足,只要有存银,我就保他平安,乱世最大需求的是平安,这就是晚生银庄的贵宾服务,也是要成本的。”
……
注1:根据许德士的记载,他经过涿州摔伤了腿,留在冯铨家养伤,带去了卢象升阵亡的消息,冯铨随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南下,去真定府祭拜卢象升,当时卢象升遗体停灵在府城东关,由于身份没有认定而无法入棺,只用草席包裹,直到阵亡五十七天后才大殓入棺,经办人就是许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