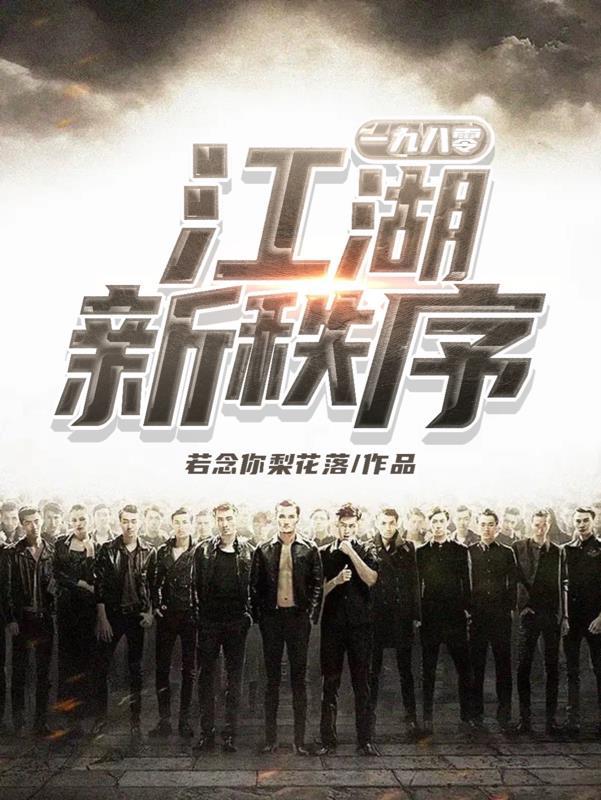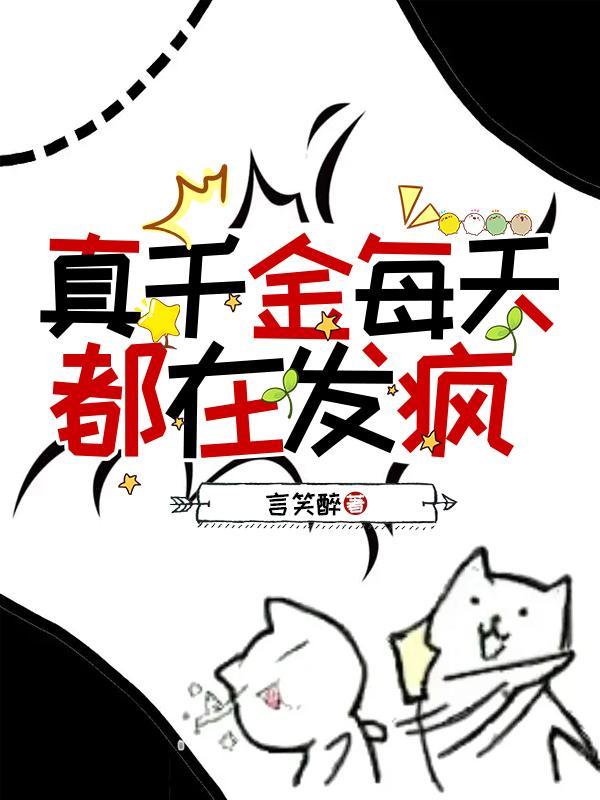爱上中文>静心禅意诗词 > 一桃花源记赏析1(第1页)
一桃花源记赏析1(第1页)
《桃花源记》(晋。陶渊明)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在写作《论语》心解的过程中,因“心内桃源”
一语而突奇想,是否陶令的《桃花源记》本来就是对“心内桃源”
的寓言式叙写呢?姑且不论陶令本意如何,而《桃花源记》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不正是因为陶令的这篇文章写出了无数人内心的梦想吗?既然佛家有“自性净土”
之说,何以不能有“心内桃源”
之论呢?所以,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原则,尝试着以“心内桃源”
为主题,重新来解读这篇经典之作,看看会有怎样的不同。
【晋太元中】,看了陶令特别选定的这个时间,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内心真正想表达的真的就是“心内桃源”
。何以如此呢?晋,既可以指代陶令写作此文的当时当下,还可以暗指【进】,即前进、进入。“晋”
这个字,本身就有“进”
的意思。进入何处呢?进入【太】【元】【中】。太,即最高、最大之意,暗指太极之心。元,即生命的根元、本元。中,即《中庸》所说的“天下大本之中”
,也是《庄子》所说的“环中”
,即中道之心。中道之心,即是与道合一之心。中,即代表了心与道完全合一后的中和状态、太和状态、元和状态。“晋太元中”
,就是进入心与道相合的道心状态。这种状态既是一种最高妙、最广阔、最博大的状态,也是一种生命最自然、最本真的本元心状态,同时亦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仁和、中和、太和、元和的生命状态、生命境界。从根本上说,这种状态正是标题所说的“桃花源”
。后文所有内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此生命状态和生命境界的叙写。故名之曰《桃花源记》。也正是因为此文所写内容暗合于每个生命中所本有的“桃花源”
,所以才能引起千古以来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共鸣!因为这篇文章的灵魂就是对生命内在桃花源的描绘与呼唤。同声相合,同气相求,始终散着桃源芬芳的文字,就像一只无形的手,静静地抚慰着天下苍生的心灵,并在这芬芳的抚慰中悄悄地传递着爱与智慧的光明。。。。。。
【武陵人捕鱼为业】,武者,止戈为武。暗指止息内心的干戈,恢复内心的清净。陵者,灵也。陵,乃是灵之栖息之地。当内心充满了烦恼、痛苦、纠结之时,心灵就不得安宁。只有止息了内心的纷扰,让心如秋天的湖水一样静静地泊息下来,心的清明、灵明、光明才会逐渐地显出来。而这个过程,也正是心内桃源逐渐显露的过程。人,仁也。武陵人,即是止息了身内外的所有纷争致力于寻求内心光明的仁者。捕鱼为业。鱼,代表了鲜活灵动的心。正是因为我们的心太过鲜活灵动,所以总是像鱼儿一样转瞬即来,倏忽即逝,极难“捕捉”
。而“武陵人”
则是自觉地、有意识的“捕鱼”
者。所谓“捕鱼”
,换成心性训练的语言,即是“观心”
之意。鱼,代表心,代表念头。纷乱的念头如鱼群一样,川游不息却又瞬间消逝。因此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注意,“捕鱼为业”
,说明这种“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