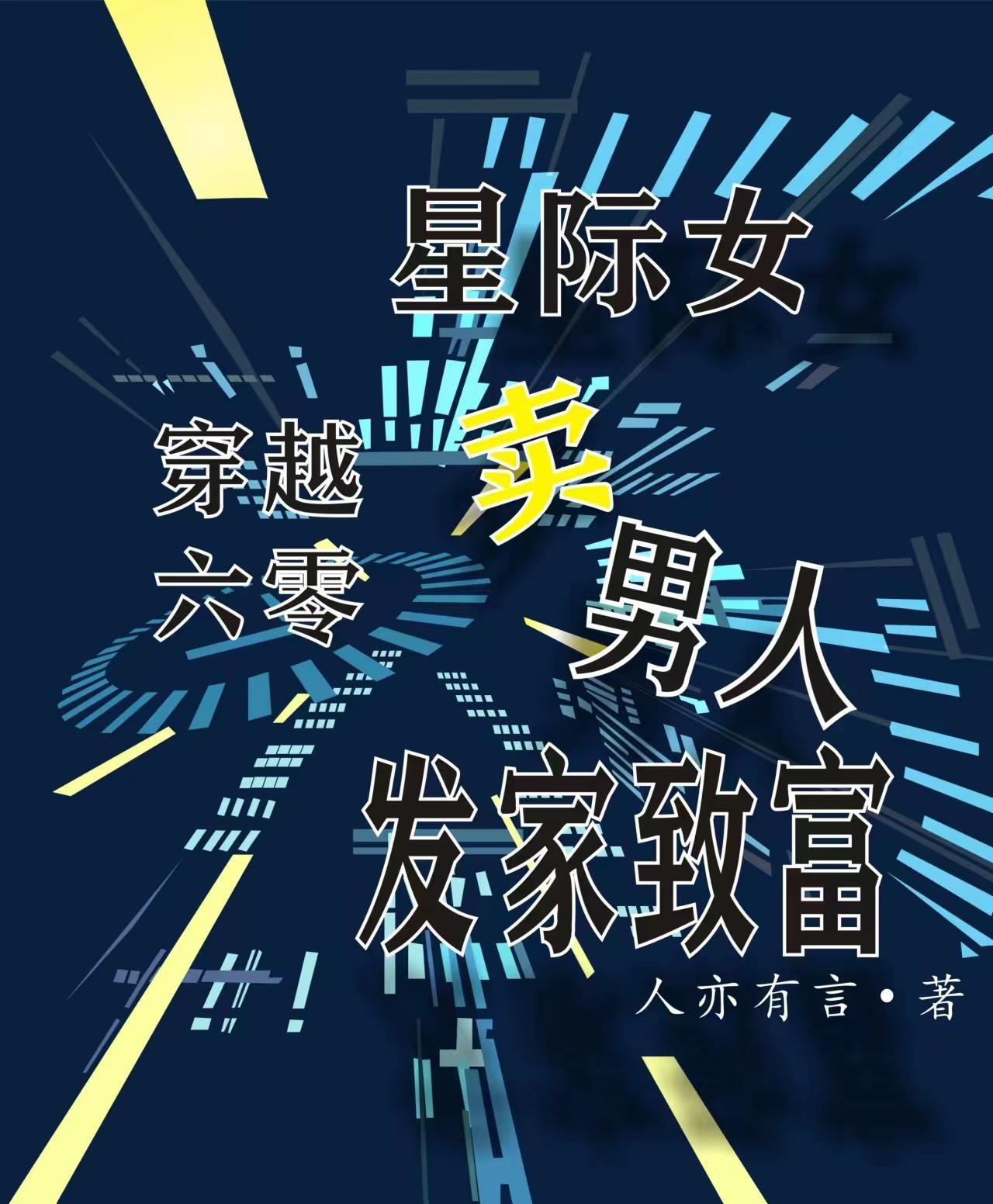爱上中文>追风望月免费阅读全文 > 第66节(第1页)
第66节(第1页)
闯入镜头的眼睛让李伟愣了愣神。
作为拍摄者,他当然知道他们现在缺了个人。孙成已经去打电话叫人过来了,只是这大雨天,来得人再快,也得几分钟后才能赶到。
倘若他现在就放下摄影机,上手t?去帮忙呢?
他拿不定主意,求助的目光向安荞看去。手里的握柄都快要放下之际,便看见安荞皱着眉头摇了摇头。
这傻小子,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种关键的时刻!
一场如此盛大的大雨,一片广袤辽阔的草原,一群为了挽救一个生命而在奋斗的牧民,一匹在死亡的悬崖上挣扎的马儿。
还有比这更完美的拍摄对象吗?
天时地利人和,什么要素都齐全了。这种拍摄的机会,多少拍摄者求之不得,寻访多年也遇不到一次,他竟然想放下摄影机!
安荞一贯推崇“直接电影”
的创作模式。
直接电影,要求者创作者做墙上的一只苍蝇,尽量不介入事件。
是坚守在摄影机背后,还是在危机时刻出手相助,这是每个纪录片创作着都要面对的伦理问题。古今中外,有的是人陷入这样的困境。
而她从来都觉得,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所有情感交集,在摄影机开机的一瞬间,就要全部斩断。创作者所做的事,只能停留在拍摄和纪录。
无论李伟将来进入哪一个流派,至少此时此刻,他在迷茫,她就要给他做出指引。
她的眼神太锐利,太笃定,给出的态度太明确。
李伟一瞬间也回过了神,赶紧趁着人物和场景的短暂固定,抓紧时间找着机位和角度。
他举着机器,在马的各个方向都拍摄着。左边肩膀不自觉地又耸了起来,安荞不动声色地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胳膊提醒了他,他又很快调整过来。
他就这样脱离出了这场事件。
身上和设备上的雨披,也让他脱离了这场大雨。
安荞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只是,她一贯敏锐的洞察力被李伟的进步和从天而降的大雨模糊,没察觉到身旁还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自己。
又是一颗雨珠子从帽檐上滑落。
苏德看着举着吊瓶的安荞,在这个夏天,他第一次感受到雨点砸在身上的冷意。
她还是发着光,哪怕是在雨幕里,指导着李伟拍摄的她,身上的光芒并未有丝毫黯淡。可他莫名就觉得,相比她在马背上散发的光芒,此时此刻她的这层光,于他而言,显得遥远又飘渺。
或许是雨太大了,糊开了很多原本清晰的东西。
摩托引擎声由远及近,带来了孙成摇来的二哥孙军。他出来得也急,压根没顾得上穿雨衣,下车的时候连摩托都没停稳,人跑到了马圈里,摩托摔进了泥坑之中。
这一下人手终于足够,李伟退开几步对上焦,专注地拍摄起眼前的画面。
驾驶舱里的孙建发再一次一点点放下铲斗,齿牙上悬挂着的拖车绳吊着马儿缓缓落在了地上。
弯折的腿被四个人在同一时间掰直,关节直挺挺的,不容它再挣脱地在地上受了力。
终于,这一次,腿直了,马站住了。
即使还有部分力量来自于上方的吊斗,可只要马腿成功地吃上劲,就不怕它的腿会彻底废了。
安荞手上拿着的挂瓶也渐渐空了,兽医插上了新的一瓶药水,拔出插进马肛门里的体温计,看了看它的体温,又推了推它的屁股。
尽管呼吸依然微薄,但这在死亡边缘的马儿的确争气,没有在推搡之中再次倒下,而是坚强地靠自己的腿站住了。
苏德、孙成和孙军三个同时叹出一口长气,放下了心。
李伟的摄影机从安荞手里的挂瓶拍到兽医手里的体温计,看到兽医要开口说话,收音话筒就差怼在兽医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