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玉软花柔比喻什么人 > 第16頁(第1页)
第16頁(第1页)
那小倌像一隻撲棱蛾子似的,翩翩飛到了長公主身邊落座。
裴時行看著那小倌故作嬌弱的瑟縮姿態,又見他媚眼如絲,殷勤地倒了酒,復又舉盞遞到長公主唇邊。
一時只覺五內皆炸。
幸好元承晚抬手止了他。
裴時行心氣稍順。
可白蛾最愛撲火,長公主此刻就是那團火。
小倌黏糊糊搭上身去攀長公主肩膀,臉也漸漸靠過去。
也不怕將長公主擠得掉下座。
這頭的元承晚自然能感知到裴時行視線,她捏住花月的腕子,絲毫不受他的撩撥影響。
「你坐過去些,本宮不需你服侍。花月,你今夜求見所為何事?若還是要我收你,話就不必說了。」
這小倌是去年自蘇杭來的,元承晚愛聽曲兒,點他唱了幾回,誰料花月聲稱對她一見鍾情,定要她納他入府。
花月哭得委委屈屈:「奴自知身份低微,再不敢奢求更多了,只求殿下日後多來玉京樓,多讓奴來伺候便是。」
長公主見他哭得真摯,只覺額痛。
但她一向對美人多幾分容忍之心:「本宮知曉了,當著這許多人的面,你莫要再哭,本宮應了你便是。」
花月得貴主承諾,破涕為笑,紅著眼睛覷她:「殿下當真?」
元承晚自是應下。
裴時行見那蛾子笑得刺眼,便知是元承晚許了什麼承諾。
他胸中怒火已將一大鍋醋都煮開了,這下咕嘟冒泡,酸意翻湧在心頭,只覺辛辣難忍。
眼見蛾子又悄摸摸探手去撫長公主柔荑,元承晚竟也不拒絕。
裴時行忘了自己此行的本意,砰地一聲擱下酒盞,嫉恨而去。
落座於他身旁之人感受到了動靜,猶自怔楞。
裴御史在席間並無熟人,所以無須打招呼。
只是這位連長公主的面子都不給了,就叫人震驚不已。
翌日坊市傳言長公主與裴時行果真不和,一方竟然自另一方宴會上吊著黑面甩袖而去。自是後話不提。
。
裴時行已不願思考明日旁人流言會如何說道了。
他早已換下那身做的衣袍。
此刻獨坐書房,生平第一遭,委屈與懊惱一遍遍叩問他的神經。
委屈的男子展開他的寶貝秘籍,蘸墨划去那條「投其所好,令她發現你二人的共同志,從而引發談興,情諧神振,兩心相鳴。」
下方一條寫的是,世人愛良才,更愛明珠蒙塵、珠玉落泥。在適當的時刻露出失意、落魄一面,抑或負傷流血。
一言以蔽,令她在對你的仰慕中產生憐惜。
他愣愣看了這條許久。
而後自嘲一笑。
她眼裡甚至沒有他,他受傷她也看不見,更遑論心疼,遑論憐惜。
她本就生於雲端,樂不識愁,亦從不把旁人心意放入眼裡。
裴時行只覺自己無比輕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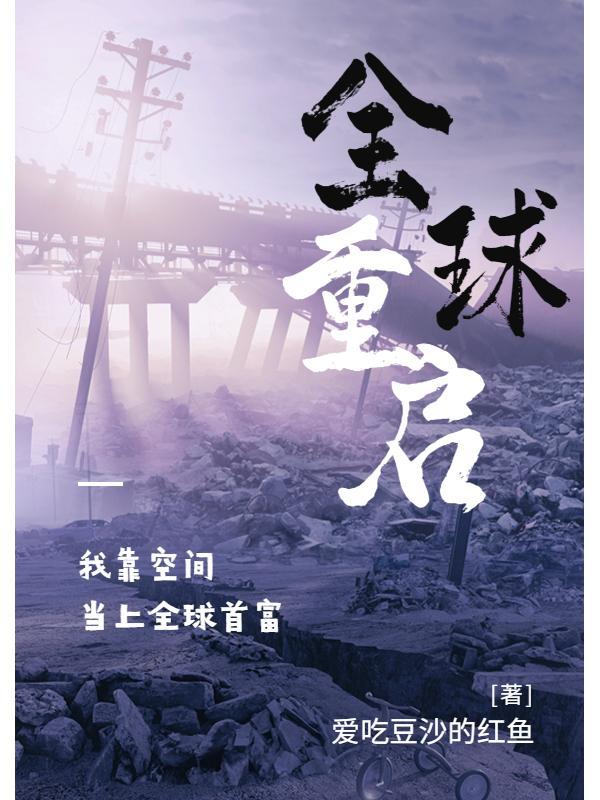
![被迷恋的劣质品[快穿]](/img/1403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