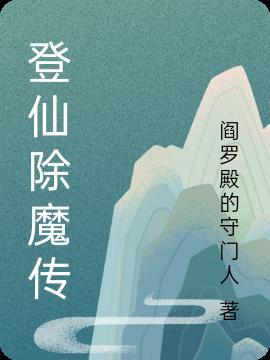爱上中文>破晓的曙光内容介绍 > 第五十九章 雪梨银耳羹(第2页)
第五十九章 雪梨银耳羹(第2页)
侯圣骁瞪大眼,又差点蹦起来:“你拿自己下注了?”
“也不是啦……是……是……”
霍心云发现没法挑片段捡着说,于是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述出来,讲完自己也心里发毛,红着脸低下头。
侯圣骁表情很不自然,按着额头不作声。
“我……我赢了。”
霍心云感觉出他有些古怪。
侯圣骁叹了口气,说:“你应该知道,你上当了。”
霍心云不知道该说什么,抿着嘴看着他。侯圣骁本来也没指望她有什么回答,顿了下说:“他敢跟你提出这种赌法,一定是有绝对的把握,首先肯定认识那两个簕殄杀手,深知这两人实力不低。你以为他在赌侥幸,其实他在让你钻自以为的侥幸空子,你刚刚说了,想走就有人拦着,这就是他们的手段,赢了钱哪那么容易走?肯定不会放过你啊!他们是看你是个练家子,又怕和我有什么联系,摸不清路数怕碰上硬茬子,才自认倒霉把你放了。还有,他的要求又含糊不清又模棱两可,两次他没有说时间期限,你这相当签了卖身契,一旦输一次,一辈子都毁了。”
霍心云整个脸全红了,听完就低下头去,头发挡下眼睛附近的半边脸。
侯圣骁自觉话说开了不太好收场,挠了挠脸抓了抓头发,咳了一声说:“没事没事,今晚上的结果总归还是好的,想骗你的人没得逞,咱还反将一军了是吧。”
“嗯。”
霍心云轻声回应。
“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即便有十足的信心,也不要拿自己去冒险。”
侯圣骁盯着她的眼睛,“答应我,好吗?”
霍心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盯了半晌用力得点下头:“好!”
侯圣骁点点头,突然变得拘谨起来,又开始抓头发挠耳朵,把装“战利品”
的布袋推到霍心云跟前,翻自己的东西找书看。开始习惯性拿出刀谱,一抬头发现这个空间很小不适合练刀,又抓了抓头发塞回去,拿出《道德经》捧在手里看。
霍心云见状又想笑又不想笑,把布袋封起来垫在桌下。人和凳子一起滑到床榻旁,翻身躺下拉过被子盖在身上,转身背过去说:“我睡觉了。”
“哦。”
侯圣骁回应一声,在桌子上抠下条小木片弹出去熄灭房梁上的挂灯,两指在桌上油灯灯芯上一捻搓燃,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书。霍心云翻身往他那里看了一眼,转身背对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夜晚安静了,凝神也只听得窗外虫鸣声不绝。霍心云睡的很好,晚上醒来一次,起身看屋里没了亮光,屏风挪动位置掩住窗格,窗帐也降了下来,侯圣骁也和亮光一起消失。她挠挠脑袋解开束发的发带取下发簪,下床走到桌边自己倒水喝。合起来的《道德经》就在茶杯旁,霍心云瞅着它发了半天的呆,把簪子放在旁边,又喝了口凉水回去拉上被子接着睡。
她不知道自己算是睡醒还是吵醒,总之就是精神头恢复的差不多,就隐约听到有人的交流声,随之是劣质木门吱吱呀呀磨着地板关上的声音,接着就睁开眼,发现天已经亮了。
霍心云理着头发坐起来,半睡半醒的看着站在门口的人。
“你……”
“嘘——”
侯圣骁倚在门上,食指封在唇边,示意她不要出声。
霍心云揉揉眼,把理了半天依旧凌乱挡在面前的头发简单得拨开到两侧,挺直身伸了个懒腰。侯圣骁又把头扭到一边去了,霍心云暗暗吐了吐舌头做鬼脸,披上层纱起身穿鞋。
紧张什么嘛,我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我就只脱了外衣,又没都脱光。霍心云撇撇嘴,在纱上打个结固定住,从床头柜拿起束带抄起铜镜,边梳理凌乱的头发边问:“刚才有人来过?”
侯圣骁试探得先看了一眼,转过头来说:“对,伙计以为他们灶房遭贼了,就到各屋看看来的。”
霍心云嘴里咬着束带,双手捋着头发朝侯圣骁看去,侯圣骁下垂的手叩着陶罐的一只耳朵,以一种别扭又费力的方式藏着陶罐,来了人只要不走进屋绝对看不到。
她很想笑,昨晚才刚打翻了两个野路子怒杀了两个杀手,今儿个早上居然亲自下厨。侯圣骁慢慢把陶罐放在桌上,霍心云迅速盘好头发,到桌前掀开上面扣着用来保温的盘子,探头去嗅里面的饭香。
她终于忍不住笑了:“你真有意思。”
“雪梨银耳羹,也找了干桂花放一起熬,就是找的梨不甜,可能糖加的有点多。”
侯圣骁挠挠头,“放了有点时间了,可能凉了点。”
他在桌上摆好筷子、勺子、碗,陶罐里也有把长木勺,霍心云拿长柄勺在里面搅了一圈,舀起来喝了一口。
“感觉如何?”
侯圣骁问。
霍心云咂吧下嘴,嚼了嚼银耳和梨肉,回答道:“有点稠了。”
“那……我去拿开水兑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