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中文>格温蜘蛛侠和迈尔斯漫画 > 第39章 什么是蜘蛛侠(第1页)
第39章 什么是蜘蛛侠(第1页)
雷蒙德·徐很及时地向格温·斯黛西那张可怜的银行卡里打了一笔钱,作为她此次行动的报酬。但还没等教授赶到洛杉矶,格温便自己硬生生地荡蛛丝一直到附近高公路,然后搭了一辆大货车回到洛杉矶,路上还打电话给自己买好了飞回纽约的机票。
她实在是不想在这里再待一秒钟了,她在这里一切的记忆最终都会指向无比惨烈的那天、指向那个在她的梦魇中预定了一个位置的场景。现在蜘蛛小姐急需要回到她最熟悉的纽约,那是她最不安全——也是最安全的巢穴。
在忙着给托尼·斯塔克擦屁股顺便招揽人心准备上位的雷蒙德来得及来任何慰问短信之前,格温就把自己的手机关机塞进了背包,登上了飞机。这次的飞行很平稳,飞行员也没染上类似上次那位的狂躁症,忧心忡忡的格温最终顺利地在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下了飞机,然后她直奔自己那个简陋的家。
于是,大街上的丧尸们纷纷回头看,往日里戴着兜帽揣着口袋好不帅气的格温·斯黛西今天像是落荒而逃一般,裹紧大衣、迈起长腿,带着风飞奔回自己家,就好像有什么要命的东西追在这金姑娘身后一般。
然后金少女重重地关上了房门,她大口喘着气,胸脯随着喘息的节律起伏着。略微回过了点神之后,她一把把装着战衣的背包甩在床上,顺着门身体慢慢滑动,最终有些颓然地坐在地板上。
少女把头埋进自己的臂弯里,让金色的丝四散垂下——兜里的手机开始“嗡嗡”
地震动。格温眼神迷茫、掏出口袋里的手机,看到雷蒙德来的短信:
“还好吗?不舒服的话可以给你放假,身体和心情好一些了再说。”
看到这条短信,格温有些烦躁地把手机也一起扔到床上,然后少女继续抱着自己的双腿埋下头去——她倒是没想什么,她也什么都不想去想,她只是需要这片刻的安静和喘息。
这天的夜里,格温甚至没挪动上床,她就只是这样抱着自己、靠着门在地板上睡着了,一直到夜里三四点的冰凉将少女从一遍遍循坏的噩梦叫醒,她才拖着那双已经麻了的腿缓缓站起身来。
开灯,往日里总拧着眉头表露出心事重重的格温·斯黛西此时只是张大嘴惊讶地打量着自己:
少女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她的眼神迷茫到几乎难以看清自己蓝色的瞳仁,额头的汗将垂下来的金色丝歪七扭八地黏着,本该柔顺地披挂在肩头的金此时显得油乎乎的,往日里总挺着的背也显得驼了下来。
“我这是……怎么了?”
格温从一切中回过头,过去的几天实在太过疯狂,以至于少女在睡了一觉、做了乱七八糟的梦之后,竟然有些难以分清现实和梦境的联系。
她现在开始疑惑自己经历的只是狂野的梦境,还是真实的残酷——她甚至觉得雷蒙德·徐这个人,乃至他所带给自己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然后少女侧头看到了半敞着的书包里露出一角的战衣,她猛地冲过去从书包里拽出那件已经被彻底弄脏的战衣,看到战衣被弹片划开的腰线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撩起自己t恤的下摆:
那伤口基本上愈合了,还剩一个疤痕,按照往常的经验,这疤痕到明天早上也会消失。
这些实打实的印记终于让格温确定了自己所记得的一切都不是梦境,都是现实。
在一晃一晃的白炽灯下,金少女手里攥着自己战衣的一角,呆立在那张小小的单人床旁,她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她有点想释放情绪,可对于蜘蛛女侠来说,哭可算不上一個多体面的方式,于是她最终还是憋住了眼泪,只是那样垂着头站着。
蚊虫和苍蝇在少女背后翩翩起舞,绕着白炽灯飞旋,好不快乐。
就在格温因为“战争创伤”
呆的同时,雷蒙德·徐则刚刚从缠身的文案工作中脱出身来——他以刚刚被托尼·斯塔克任命的斯塔克工业总顾问的身份签署了一长串有关解除奥巴代亚·斯坦职务、冻结其股权和起诉其本人的文件。
托尼给的这个“总顾问”
,换句话说就是代理席执行官——至少是半个席执行官,另外半个属于小辣椒珮珀·波兹。
如果要用雷蒙德自己熟悉的东西打比方的话,现在的他类似于万历朝的张居正、帝国辅上柱国,珮珀·波兹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他俩达成一致才能行使统治整个“斯塔克王朝”
的权力。
这也算是托尼·斯塔克本人顺理成章的吃一堑长一智了,他不会再把公司的所有大权交到一个外人手中,最终反过来危害到自己——当然这些花花肠子,托尼·斯塔克自己不一定能想清楚,这或许只是出于他的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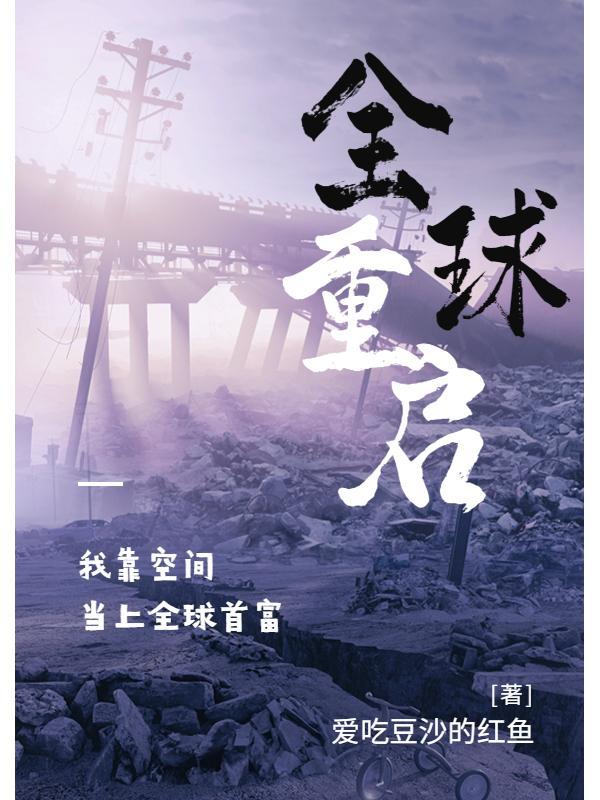
![被迷恋的劣质品[快穿]](/img/1403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