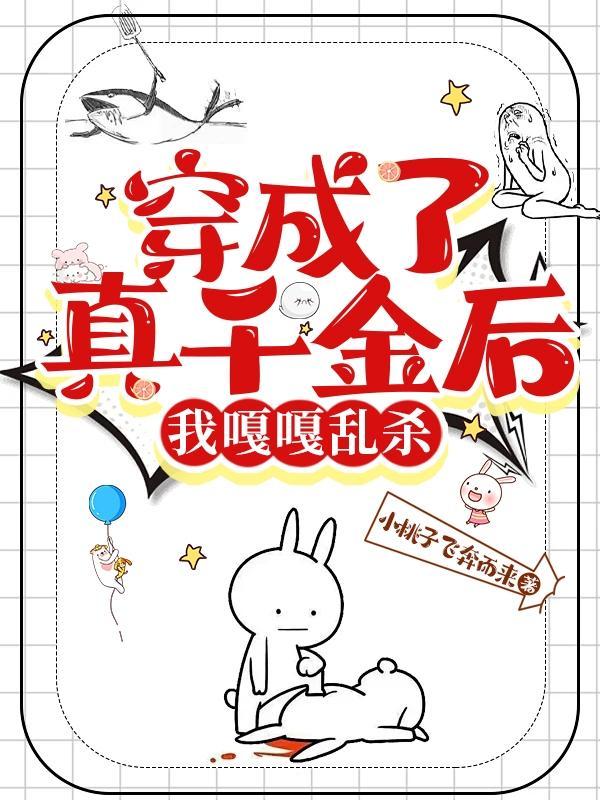爱上中文>今天风也晴朗穗禾 > 第73章(第2页)
第73章(第2页)
一个小时前的消息,徐漾没回。
他直接播了电话,铃声一直在响,已经没有耐心听后面烦躁的机器音,挂断电话,快步出了门。
……
夜幕沉沉,晚上七点,民宿小院灯柱亮起了灯,两三个年轻姑娘聚在桌边撸串聊天。
以往这种热闹场景都能看到徐漾。
周泽树抬头,她独住的那栋小楼,黑漆漆的,没亮灯,不见任何回来的踪迹。
刚刚来的路上,特地去了里屿,门早已经锁了,人也不在那。
他一瞬就急了,抓了把头发,整颗心七上八下的,唯恐会出什么事,脑子里疯狂搜刮着到底还有哪些地方能去。
其中一个女孩第一眼瞧到周泽树,热情招了招手:“周老板,你来找徐漾啊?”
“嗯,你们有知道她去哪了吗?”
女孩奇怪:“她早回来了啊,楼上吧,我没看下来,可能有点不舒服,问她要不要下来玩,说早些睡了,哦她今晚状态不太对。”
明明中午还好好的,她还说要等他回来。
周泽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没见过这样的徐漾。
从认识开始,从没见过她这副样子。
屋里晦暗没开灯,却能依稀看得清人影,坐在床边的人紧紧抱着膝盖埋头小声呜咽。
她在哭。
“……徐漾。”
—
—
以自我的角度去同化别人,这算不算一种罪恶?
归根结底,每个人的人生课题不同,擅自剥夺对外看世界的能力,是否太过残忍。
徐漾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她麻木坐在路边休息椅上。
想不通。
手上紧攥着藏在桌底下的药板和美工刀。
她无法将这两样东西跟周泽树联系到一起。
那样体贴温柔,无声默默照顾着大家的人,怎么可能呢?
周泽树……
徐漾发现她好像忽略了很多。
他身上偶然流露出的令人怀疑的孤落和挣扎。
他有时候唇色苍白,食欲也不怎么高,曾经问起来,他只是云淡风轻地说,夜里没睡好,就另玩笑着擅自将话题轻易带开了。
平川之旅,她意外撞见他双手冒着青筋撑在洗手台上,很久很久,抬头时镜子里那双蓄着泪发红的眼。
徐漾永远记得那一幕。
她完全懵了,忘记做任何反应,呆呆地站在他身后。
列车在远方行驶,灯光暗淡,她分不清眼前的人。
究竟怎样的眼神。
无助,脆弱,像历经一场倾盆足以淹没的雨,不知来来回回多少次,慢慢潮退后的料峭与凉淡。
可在转身看到她的那刻,他又扬起了不让任何人生疑,温暖的笑。
临走的前晚,他说徐漾我曾经看不到世界的颜色了。
风吹着绿化,头顶是高大的楸树,落了一小片缺了瓣的花,被风卷着在地上蹁跹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