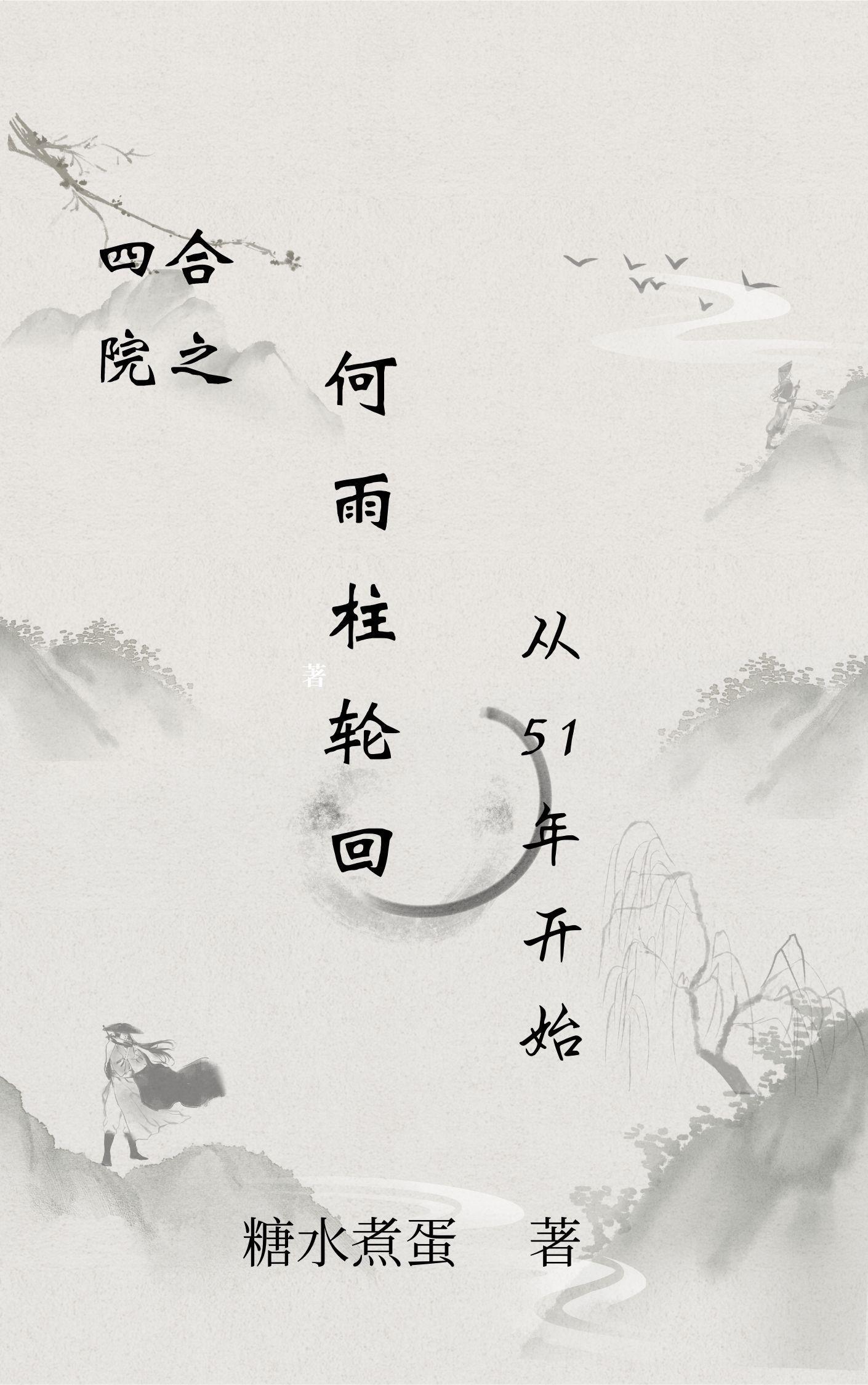爱上中文>弦溺TXT > 第77頁(第1页)
第77頁(第1页)
像他這樣身家清白,還要上趕著往火坑裡跳,實屬罕見。
「我不知道,但我需要錢。」
「目的還挺純粹的,我欣賞你。」
鐵板釘釘,他被破格錄取。
市局有自己的衡量標準,會根據戴罪立功的表現來減輕量刑,或是給一些等價的交換。
時祺在成年後自願成為南江警隊投在城市中的一枚棋子,有直屬聯繫的上級。蹲點隋夜是他做過最危險的一件事,也是在那個時候,上級決定不再讓他冒險。
「真沒想到,你小子還有幾分本事。」
「不錯,是個干刑警的好苗子。」中隊長在病房裡對他說:「倘若畢業後你願意來這裡,我隨時歡迎。」
可惜他志不在此。
在四處遊蕩捕捉線索的過程中,他會在南江的各處流動,對任何微弱的風吹草動都了如指掌,也極易結仇,腹背受敵。
這就是他所能說的所有故事。
-
「走吧。」
時祺無聲地笑了笑,「今天你聽的故事夠多了,足夠讓你好好消化一陣。」
「你感興,我以後隱去姓名和背景,再講給你聽。」
他們從露台往下走,才發覺晚上忽起夜雨,滴滴答答落在草坪上,激起濕漉漉的草腥氣。他們沒有帶傘,時祺就將千鳥格西裝脫下來,頂在頭上,給溫禧當作擋雨的工具。
「還有什麼想問的嗎?」
記憶中的溫禧定會掘地三尺,刨根問底。
他以為溫禧會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二十歲時難以啟齒的事,到現在不過是被風吹起的一張薄薄的餐巾紙,捲走便杳無音訊。
他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溫禧,自己缺錢。
「受傷的時候,會覺得疼嗎?」
未防溫禧小心翼翼地問。
他的心神微動。
時隔經年,她卻依然在乎他身上的那些斑駁的傷痕。
她在與他共情。
「早就不疼了。」
他看向她的眼睛映上了些別樣的溫柔。
為了一點似是而非的線索,他也混進過本市最大的幫派,群架時他沖在最前面,卻又遵紀守法不敢動手,只做正當防衛,頭破血流是家常便飯。
為了節約醫藥費,蜷在出租屋裡給自己沉默地療傷。
「溫禧。」
他復又鄭重地叫她的名字。
「我跟你說這麼多,你一直知道我的目的只有一個,我也表現得很明顯。」時祺又說。
「我。。。。。。」
「時祺,我今晚答應了宋小姐的測試,」溫禧及時將他最關鍵的話打斷,避重就輕地引開話題:「你說她的測試,會安排在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