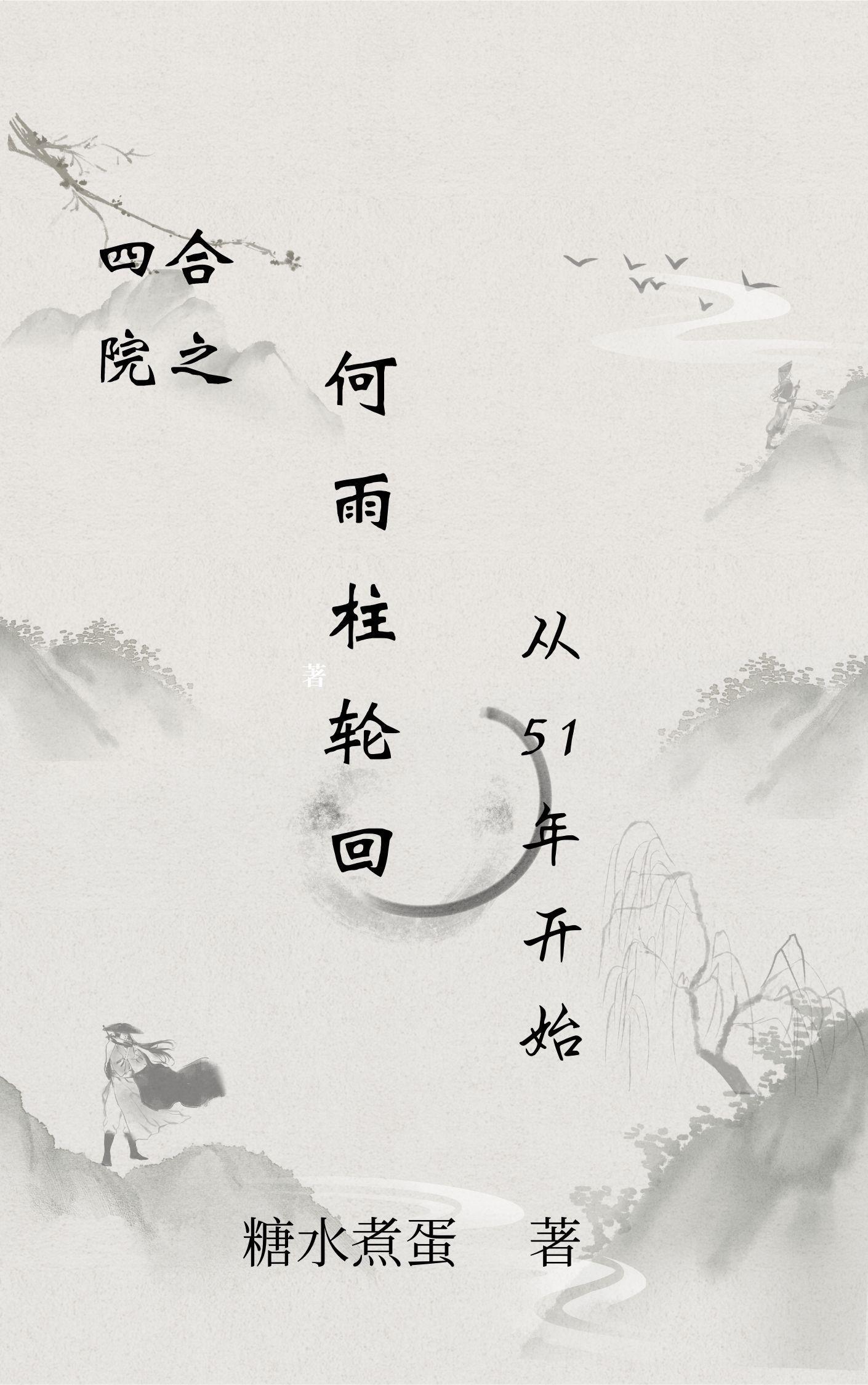爱上中文>大佞臣 沉默的戏剧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可自从成年之后,沈容却屡屡压他一头,他科举落第,沈容却高中探花,他是五品相吏,沈容却是四品侍郎,他想尚公主,沈容却与二殿下亲密,甚至托了北远侯去提亲。
沈容看似云淡风轻与世无争,却总有出其不意的大胆行径,朝堂上下对他可谓是毁誉参半,可即便如此,沈容依旧在圣上及百官面前留了脸,而他沈康在朝中却仿佛查无此人一般。
五品相吏无需上朝,且自从他私盖官印之后,父亲也对他限制了许多,只叫他在相部做些无关紧要的杂活,甚至连议事厅大门都不准他踏入一步。他原本也是好意想替父亲分忧,因着戴震科一案,父亲日以继夜疲惫不堪,累得双目血红,他不过是想让父亲睡个好觉,只私做主张了一回,哪知运气不好,偏是那一回捅出了大篓子,他如今想来仍觉得是那尚书院害他不浅。
昨日得知北远侯去向圣上提亲,被圣上狠狠训了一顿,还被砚台砸了脸,那北远侯是什么人,他可是圣上红人,圣上再咣火的时候也不曾打过他脸,他顶着满头墨汁从御书房出来,大摇大摆走到宫门外,沿途叫人笑话了一通。当日沈相得知后,便将沈容大肆训骂了一顿,甚至口不择言骂了一些粗鄙言论,沈康在旁听着暗自痛快,总觉得沈容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可今日去了相部,却不见人鄙夷嘲笑他,同僚们多半是当个乐子听听罢了。
沈康往日谨记父亲教诲,自持清高,从不愿与人多交际,今日放下架子去找同僚探了探口风,探花、相府嫡子、北远侯外甥,这些名头一个个冠在沈容头顶,加之他平日姿态谦卑,性格柔顺,与谁都能温言几句,若非二殿下乃皇子,又是圣上心头肉,这段姻缘可谓是佳偶天成。
沈康今日方知,他在相府争那一亩三分地的时候,沈容早已越过他去了更高的地方。
沈康敛了敛心神,蹙起眉道:“娘,我是男子,衣裳只是点缀,不必如此费神,你拿去给自己做衣裳吧。”
康姨娘见他心情不悦,遣了人都出去,拉着他坐下,缓缓问道:“今日是怎么了?如此心神不宁?”
沈康不愿与她多费口舌,只说:“沈容要去尚皇子,我心里总是不安心。”
康姨娘倒了杯茶来喝,哼笑一声道:“自古以来只有犯了错被圣上厌弃的皇子,才会做赤子出嫁,三岁看八十,沈容这厮从小就是无法无天,做他的黄粱美梦去。”
康姨娘又将那布料拿出来看,见沈康仍是愁眉不展,继续说道:“且他越过你父亲,找了舅舅去提亲,这本就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之事,圣上怕是看清了他的嘴脸,更不会许他好亲事。”
沈康却是道:“沈容这佞臣惯会胡搅蛮缠,他口蜜腹剑,擅长阿谀奉承,若是当真被他娶了二殿下为妻,我如何还能尚公主?自古没有一门结两次皇亲的先例。”
康姨娘不以为意道:“你父亲是当朝宰相,相部之,圣上岂会不听他的意见,沈容这门亲事非但成不了,还会坏了他名声,他结皇亲不成,惹了御前盛怒,皇城中勋贵世家谁还敢往前凑?倒是些小门小户的小姐赤子,还有些机会。”
康姨娘给沈康倒了杯茶,推了推他,逼着他饮一杯。
沈康闷了口茶道:“好,沈容的事情暂且不说,我的亲事又如何,你与父亲想为我尚公主,又何必再办什么茶宴?”
“哎哟,我的大少爷,你真是一点都不明白娘的苦心。”
康姨娘唉声叹气道,“你如今官职不高,娘日前探过你父亲口风,没有平白无故升官的道,你得熬些资历出来,你既官职不高,若想尚公主还得多在官眷面前长长脸,得了她们喜欢,名声传了出去,才能叫后宫娘娘们都知道了你这个人物。”
沈康琢磨了半晌道:“去年春茶宴,皇后娘娘请了我与沈容一道去,确实也对我夸赞有加,只是后来便不再有动静,再有茶宴花宴也不曾叫我与沈容过去。”
康姨娘拍拍他的手:“如此就是了,你得多走动,叫那些皇亲贵戚们替你吹吹风,多进宫参加宴会,若是四公主自己相中了你,那才是真正水到渠成。”
沈康恍然大悟道:“娘这一招叫做另辟蹊径。”
康姨娘笑道:“为娘懂什么招数,不过是听你祖母说过些相看的门道。相爷自小疼爱你,将你当成嫡子一般养大,你虽是庶子,那也是相府庶子,身份十分尊贵,若是公主与你情投意合,想必圣上与皇后娘娘也说不出什么拒绝来。你如今要做的,就是好好装点自己,留个好名声,明白了吗?”
沈康恳切道:“孩儿明白,母亲深思熟虑,确实是孩儿考虑不周了。”
康姨娘拉起他手道:“康儿来,过来挑挑衣裳料子。”
此刻畅忧阁里,陈氏母亲急匆匆赶了过来,陈夫人笑吟吟将茶端出来,满面笑意道:“母亲怎么来了,若是有事遣人来传,女儿过去就是了,何苦你跑一趟。”
陈老夫人恨恼道:“你怎得还笑得出来,我听说北远侯去给沈容提亲,要娶当朝二皇子?”
陈夫人颔,将绣了一半的绣棚端起来,笑说:“是有这么一回事,昨日叫相爷骂了一顿,又在祠堂罚跪了一宿,今日上朝去了还不曾回来。母亲过来坐,瞧瞧这幅帕子绣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