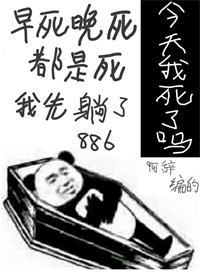爱上中文>爱在两千公里外好看吗 > 第24章 母亲(第2页)
第24章 母亲(第2页)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你为什么从来不反省你自己?你就没错吗?”
这是张钰每次吵架的必用台词,他觉得很可笑,他一向以理智行事,怎么会有错呢?
以理智行事的人就没错了吗?
现在他觉得自己错得离谱。
他看到破败的平房门口站了一个老太太,白发苍苍,紧紧抓着门框才勉强稳住摇摇欲坠的身体,她在发抖,大口大口地喘息,鼓足勇气才向前迈了一步,两步,布鞋底蹭在土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两条腿颤颤巍巍地往他的方向挪,生怕走得太快会吓跑这归乡的游魂。
“妈。”
他叫了一声,老太太站在原地愣了一秒,下一秒踉跄着冲过来把他死死抱在怀里,滚烫的热泪在她沟壑纵横的皱纹里流淌,又滴落在他脖子里,灼烧他陈年的伤疤,烧得他痛彻心扉。
“儿子,我的儿子,你遭了多少罪啊?”
她哭得直不起腰,苍老褶皱的手抚摸着儿子破碎的左脸,
“没事,没事的,受了点伤而已。”
可他越是说没事,做母亲的就越是难过,他只好握住母亲的手,笑着说:“妈我饿了,有饭吗?”
母亲像得了某种恩典,浑浊的眼睛瞬间被点亮,在昏黄的灯光下熠熠生辉,“有!有饭!快进来,妈给你做饭吃!”
简单的茄子焖饭,他小时候经常吃,吃得都想吐,现在吃也还是原来的味道,但他竟觉得这是他有生之年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在上海的十几年他一直胃口不好,有时候忙起来就随便塞块饼干对付一下,正儿八经吃饭也是吃几口就饱了,而他大多数时候也没耐心陪别人吃,把单买了就自顾自走了,
原来他的胃比他更想家。
饭后周荣抢着把碗洗了,而母亲还是一分钟都闲不住的操劳性子,转个头的工夫就坐在炕上忙针线活去了,周荣则坐在桌边帮她剥剩下的豆角,
两个人都有一肚子话想说,却偏偏生疏着不知该从何说起,
“荣啊,你……成家了吧?”
“结过一次婚,离了。”
老太太眼尖,看到儿子手上的戒指,却犹豫着不敢问,周荣多聪明啊,老娘那欲言又止的样子,等于把想问的都问出来了,
“这是和二婚老婆的戒指。”
二婚老婆,真难听,但似乎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词汇了,其他所有词汇,再好听都是粉饰太平。
“哦。”
这短短几句对话,信息量有点大,老太太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只好先低头穿针引线,过了好半天才再次开口,
“那,那你有娃了不?”
“好像有,反正她怀了,如果是我的,现在应该两岁半了。”
这一记绝杀,老太太何止是消化不了啊,她心脏病都要犯了,脑袋瓜子嗡嗡的,只觉得眼前有好多小星星,
“这……你这,那她现在人呢?我倒要去问问她去!天底下哪有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
老太太捶胸顿足,把针线筐摔得乓乓响,但她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不知道,找不到人。”
……空气突然安静,老母亲跌坐在床上,觉得还是死了比较好。
“妈你别生气,不是她的错,是我的错,她是个好姑娘,其实我们还没领证,是我一直不肯娶她,我耽误了她,她生我的气也是应该的。”
他剥完最后一个豆角,拍拍手转头望向母亲,
“妈,那么多年你一个人带着我,吃了很多苦吧?”
母亲低下头,出神地望着缝了一半的衣服,半晌才憨憨地笑一笑,“苦啥呀,不是还有你奶奶么?你爸跟野女人跑了,可你奶奶一直对咱们娘俩挺好。”
周荣凉凉地笑一下,抬头望向窗外,天真黑啊,连一颗星星都看不到,
“我奶奶死的时候我才几岁啊,那时候你上海家里两头跑,我又是个不省心的,天天跟人打架,害你吃了那么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