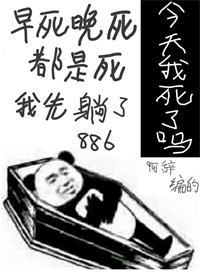爱上中文>女主重生改嫁文 > 第1章 纳妾(第1页)
第1章 纳妾(第1页)
窗外已是冰封天地,朔风凛凛,冬寒卷过回廊,窗棂上都结了霜。
青禾提着新炭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自家姑娘正开着窗子,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大雪纷飞。
她上前将窗子合上,“姑娘,您身子还没好呢,仔细又着凉了。”
青禾是陪嫁丫鬟,从姑娘闺中时就伺候着,就算姑娘嫁到了太傅陈府为嫡长孙妇,她也没有改过称呼。
邵文瑜握着几乎已经没有了什么热气的手炉,“不知父兄在千里之外的苦寒之地如何了,那日走得匆忙,也不知给他们准备的袄子够不够。”
“还有阿淼,她本就身子弱,那种地方她该怎么挨过去……”
青禾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半晌后,她将话题转到刚取的炭火上,“姑娘,高婆子越来越过分了,今日分得尽是些粗炭!”
粗炭烟大迷眼,从前就是下人都不会用的。
邵文瑜慢慢转身回头,视线落在火笼旁的那一筐炭上,“府中各房的用度本就有限,夫君被贬了官职,可能家用紧了,敲碎了慢慢用吧。”
青禾咬了咬唇,“奴婢分明瞧见表姑娘房里的梅香取的是上好的银丝炭。”
邵文瑜的手指骤然收紧,精致的手炉上刻着朵朵盛开的荷,此刻热气散尽,掌心一片冰凉。
片刻后,她缓缓松开,将手炉放在一旁的矮凳上,垂眸掩下一片暗淡。
“表姑娘来者是客,哪有让客人用粗炭的道理。”
青禾看着姑娘苍白的病容,嘴唇嗫嚅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什么客人会在府上住两年,从最开始的避祸,到现在俨然已经把自己当做女主子了。
自家姑娘这个正室夫人,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咳咳。”
邵文瑜忍不住喉间溢出断断续续地轻咳声。
青禾赶紧取过榻上的狐裘披风披在她的身上,“您看您,又开始咳嗽了,病不见好,还要开窗子。”
邵府被判流放那日,姑娘在大雨中跪了一天,也没能求得太傅的开门一见,那晚被姑爷带回来后就开始高烧不断。
好不容易将养得大好,却又传来消息,夫人在流放的路上,病体不支去了,姑娘当即就昏死了过去。
再醒来,腹中的孩儿也落了。
此后,姑娘的身子就像秋风中的枯叶,一日比一日消瘦。
大夫换了一茬又一茬,却始终不见好。
邵文瑜扶着桌角,一阵轻咳似乎都要耗尽了她全部的气力。
她喘着气看着自己苍白得近乎透明的十指,唇角不觉勾起嘲讽一笑,她何时这般柔弱了,曾经她也是个艳阳下纵马恣意畅笑的姑娘啊。
“吱呀”
一声,门被推开,雪花夹着刺骨风跟着来人钻了进来,落在地上瞬间化成一滴滴水珠。
陈知行解下披风,他看到窗边的矮榻上,瘦得几乎判若两人的邵文瑜时,忍不住皱起了眉来。
不过才七八日不见,怎么就瘦成了这副鬼样子!
“邵氏,你若还是赌气,糟践的是自己的身子。”
“岳父被陛下降罪,岂是我陈家能左右的,莫非要我太傅府上下百余口跟着一起去流放不成?!”
邵文瑜见他旧事重提,毫无血色的唇又白了两分,扶着桌角的手背上青筋毕现。
陈知行的话音落后,屋子静得只有火笼里的炭火“噼啪”
声。
半晌后,她才寻回自己的声音,“我爹的遭遇与太傅府无关,是他自己为官不慎,有此一劫是他命中注定。”
邵文瑜一字一句,就像重新撕开那一日的伤一样。
她爹没有贪污,他荐举了曾经的下属,下属得了肥差,知道她爹喜欢问溪先生的画,特意寻了两幅送来。
她爹一眼就看出了是假的,人家特意送上门,他也不好拂了面子,便原封不动地锁进了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