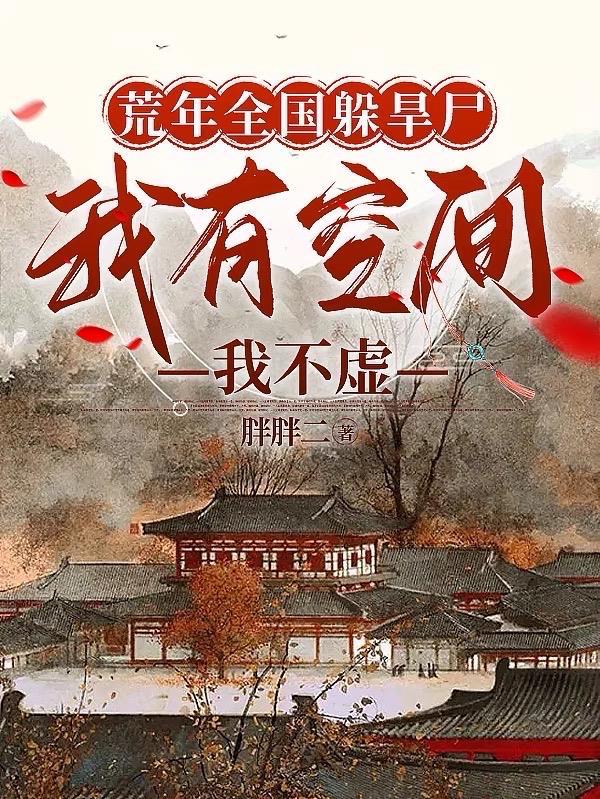爱上中文>慕娇靥望烟全文免费TXT > 第 129 章 八(第3页)
第 129 章 八(第3页)
祁肇扯下嘴角,眼中微冷,“你当他是好心?难道不是过来亲自监视?”
一个堂堂国师,竟然这个时候过来,怎么想都是蹊跷。让他不免会想到惜玉,有渤泥国师在,他要带走她还真不好办。
想到她,就会想起那晚的阴暗林子里,他病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她决绝转身离开,头都不回。
是否那个时候,她想的是让他死在那里。是不是在边城的那些时光她都忘了?那时候他哪怕一点儿的伤,她都会很上心。她对他好,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那样简单纯粹的好。
那次大雪,被困在城外荒山上。山洞中,他摔伤了腿,是她给他生火,一直帮着他。后来她睡着了,竟然无知无觉的靠在了他身上。
他记得自己当时轻轻抱住了她,说,“惜玉,以后跟我罢。”
睡梦里的少女嘤咛一声,他把这当成了她的回应。
“那咱们这边如何应对?”
胡大人问,见着祁肇想从床上下来,赶紧道,“大人,你的病没好,不能乱动。”
祁肇仿若未闻,撑着从床上下来,换来了剧烈的喘息。他走到窗边,看去三湾镇的方向。
“必须起来,我们不能在渤泥
待太久。”
他眯着暗沉的眼睛。
总是要带着船队去西洋,留给他的时候并不多,这期间一定把惜玉找回来。
胡大人一脸担忧,两天的病痛,已经让祁肇瘦得脱了相,可是情况仍不见好。上次好不容易运回来的药材,只是杯水车薪,热病传染的太快。
要说渤泥国师过来这边,多少是察觉到热病,所以不希望大渝船队的人上岸乱走。
又是雨天,到处一片泥泞。
船靠上了三湾镇的码头,祁肇撑伞走到船头,抬手挡唇咳了几1声。渤泥没有冬天,可他竟感觉到了寒意。
他站在雨里等着,直到看到那抹纤柔的身影出现,目光渐渐变得柔和。
“大人,你有什么吩咐让下官去办罢。”
胡大人追上两步,看着想下船的祁肇,脸上满是担忧。
祁肇踩上跳板,脚步微微一顿,声音很轻:“不必。”
胡大人没有办法,眼看着人走下船去,踩着泥泞的路前行。他不明白,只是一个当然逃走的侍妾,祁肇为何这样执着?
祁肇自然不知道胡大人现在的担忧,一步步的朝着那间酒肆走去。风雨中,店外木杆子上悬挂的幡旗已经湿透,上面只有简单一个字:酒。
他的脚陷进泥里,是黑色的泥浆,最后终于站在酒肆外面。
伙计迎出来,大渝人和渤泥人很好分辨,是以便招呼着,让客人里面坐。
祁肇不语,弯腰把收起的伞支在门边,低头整理着自己的衣衫,确认每一处都整齐,这才进了酒肆。
他环顾四下,然后径直往后面走去。
伙计见状想阻拦,被后面跟着的侍卫拦住,一把宽刀落在肩头,当即吓得不敢再出声。而店门,此时也被人守住了。
祁肇站在门帘外,手指碰触上粗糙的帘布,耳边听见里面噼里啪啦的算盘响。顿了一顿,还是伸手挑开了帘子。
里面的女子察觉到,抬头来看。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相交。
并没有预料中的尖叫躲避,祁肇现对于他的出现,惜玉如此的平静,甚至在账簿上记下了一个数目。然而,这样的她却没让他觉得惊喜,只是心底更凉,她现在甚至连厌恶都不愿给他了吗?
“惜玉,我想带你走,”
他走进去,隔着桌子,“我会改,你信我一次。”
惜玉面色淡淡,手里账本一合:“祁大人,我已经嫁人。”
短短几1个字,让祁肇眼前黑,以为自己听错了:“不可能,你怎么能嫁人?你分明……”
“分明什么?”
惜玉打断他,眸中无波无澜,“女大当婚,再平常不过。”
她当然可以嫁人,只要那人对她好,信任她,她为什么不呢?难道一直沉浸在过去的阴郁中吗?
“咳咳咳!”
祁肇猛的咳了几1声,下意识想找杯水,可是没有,面前的女子再不会像在边城那时,对他上心照顾。
“大人病重不该乱走,病气过给别人总是不好。”
惜玉道了声。
“你骗我,”
祁肇眯眼,深沉的瞳仁中闪过熟悉的阴戾,“我不信你会嫁人,惜玉,要说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
忽的,惜玉笑了声,银铃般清脆。
“祁大人说了解我,所以才想一点点拆了我的骨头吗?瞧,你根本不会改,永远都不会。你宁愿抓我回去,看我慢慢枯萎而死,也不愿松开你高贵的手指,因为你从来都当我是个物件。”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