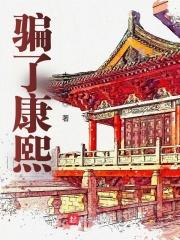爱上中文>什么叫下等婚姻 > 第54章(第1页)
第54章(第1页)
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不敢逾越。
晚上七点,刘姐做了几个家常菜,我坐在桌前,没什么胃口,问她:“今天傅先生会回来吗?”
“应该会。”
刘姐用很委婉的措辞告诉了我答案。傅晏礼要回来,基本上会提前跟刘姐打招呼,没有说,百分之九十九都不会回来。
随便应付了两口,我上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傅晏礼什么都不缺,也不要我的爱,那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他?
他接连几天都没有回来,也联系不上他。
我每天嗜烟,脾气越来越差,只要一点小事就能让我破口大骂,刘姐和元宝都尽可能的离我远点,以免惹我生气。
我知道我不该这样堕落下去,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在怀疑,当时让傅宴礼救我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凌晨十一点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拿起床头的烟和打火机,走到楼下。
夜已深,路灯伫立在黑暗中。
今晚没有月亮,乌云压着天际,看天气预报说有雨,在凌晨一点左右下。
点燃了烟。
一阵风吹进来,习惯了新城的早晚温差,这个风算得上温和,甚至吹在身上都没有什么实感。
客厅没有开灯,一点点光从窗外透进来。我指尖夹着一根烟,瘫坐在地板上,抬起头,望着天花板。
我明白,我必须找点事情做,不能让脑子停下来。
一旦停下来,就会想太多不应该想的。
“啪嗒——”
黑暗如潮水般退去,一道身影笼罩着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指尖中的烟被夺了去,鼻间被一阵寒冽侵袭。
傅晏礼脱下外套,不耐烦地扯了扯领带,深深地吸了一口,可能是廉价香烟的味道不怎么样,他直接将烟点灭在烟灰缸里。
外面闪起雷火,客厅的灯光太明亮,要不是那响彻天际的轰鸣声,我也不会注意到外面打雷了。
我嘴里又苦又干,明明是睡觉前刷了牙,喝了水。
傅晏礼随意地取下腕表,那根短的指针走在一和三之间,稍长一点的在六和久之间。
由于特殊性,仿佛只有最长的那根在转动一样。
其实就这么坐着怪尴尬的,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主动挑起了话题:“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傅宴礼脸上挂着疲态,声音不紧不慢:“等一段时间吧。”
他似乎很疲惫,已经闭上了眼睛,倒在沙发上。
我默然,绕到他的身后,给他做头部和肩颈的按摩。
手法熟练,力道适中,他的表情完全松懈了下来,发出浅浅的呼吸声,好像睡着了。
按摩了将近半个小时,看着他闭着的眼睛,我心一动,捧着他的脸颊,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
这个吻很轻很轻,只是蜻蜓点水般落下,又腾飞起。
我起身,不知何时他睁开了眼睛,黑色的瞳孔干净,犹如一对上好的黑曜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