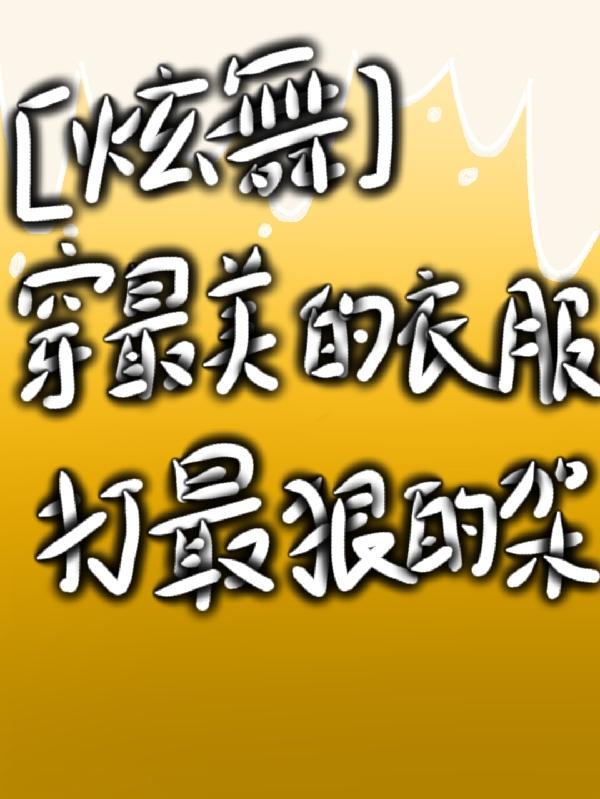爱上中文>墨燃丹青男主是谁 > 第一百零七章 相逢的乖乖(第1页)
第一百零七章 相逢的乖乖(第1页)
画画的人,皆长着一双骨骼分明的大手。
此时,这双大手果断地抚上贺水光鬓散乱的面颊。
山月低低垂头,紧紧抿唇,唇色泛白,眸光却无比坚毅:若是水光想不起,那便是最好的安排,她还是平宁山中欢快肆意的小猴子;
但,若是想起来了,那便面对。
历经的过去,如覆水,如落尘,如出口的话,如敲下的章,无法改替,更不能销毁。
唯有面对,别无二法。
哪怕,一边蜿蜒滴血,一边艰难面对。
山月尖尖的下颌虚放在水光颅顶上。
少女头顶调皮的碎轻扎着姐姐的皮肉,一下一下地,像刺进早已干涸的心田。
水光先是呜咽地哭,小小声抽泣,慢慢地声音放大,企图将强压在心底深处那一块碰不得、摸不到的恐惧与委屈全部宣泄干净。
山月紧紧环住妹妹,静静地等待着水光平复。
魏大夫与魏陈氏相视一眼。
魏大夫电光火石间,终于明白,为何这位向来冷漠的未来御史夫人,每每至魏家总是和蔼可亲,还跟菩萨降世般,给他们宅子住、帮他们跑东跑西。
嗯,他一度以为是因为魏家人热闹快乐的气氛感染了贺姑娘。
如今看来,着实是他多想了——全因他们手里握着如春啊
魏大夫做了个手势,与妻子一并退出堂屋。
不知哭了多久,水光死死揪住姐姐的衣袍宽袖,抽泣渐渐平复,抬起头,双眸含泪,声音嘶哑:“娘,娘亲最后死了,是吗?”
山月面色如常地垂下眸,一眨眼,一滴泪直直垂下,命运巧合般,与水光的眼泪触碰融合。
水光扯出一抹难看的笑:“我让娘跟我一起藏在水里,娘却回头折返寻你——”
水光头痛欲裂,在尘封已久落满灰尘的记忆中翻找。
火光之中,邱二娘的面孔愈渐清晰,她披头散,嘴边凝固的鲜血像戛然而止的乐符。
“娘!娘!你别去!你别去!”
她大哭着抱住邱二娘的腰:“姐姐要我们活着!”
娘的舌头被割断,已说不出话来。
娘缓缓地抱住了她,短暂地环抱了一瞬,便放开了。
娘拍拍她的肩,淌血的嘴角微微勾起,像是在笑,眼神温和,却从未如此坚定过。
娘手指了指火光中。
没有言辞,但她一瞬间便明白了娘想做什么。
娘想陪着姐姐。
就算下黄泉,也母女相伴。
烛火点双数,四盏蜡烛分列东西南北。
在昏黄烛光连成的模糊的光影中,水光仰起头,鼻涕与眼泪糊作一团,她想笑,却没有力气抽动嘴角:“我真没用,我怎么能忘了呢?我怎么能全忘了呢?娘和姐姐拿命让我活,我却全忘光了!怎么有我这么没用的人啊!”
水光歪着头,狠狠拿手拍头,呜咽与低泣像常常鸣唱的诗,在无意识呢喃数十年后,方知其中意。
山月一把锁住妹妹的手,紧紧环抱住水光,泪水一行咬着一行快滑落。
水光泪意朦胧伸出手:“姐姐,你长大了,是这个样子的呀”
冰冷的指尖,眷恋地一寸一寸抚过山月的眼、鼻、口。
“是我的错。”
山月声音颤抖:“是我的错我悔了十年,恨了十年,怨怼了十年——我做什么自作聪明!我做什么要带你和娘去另一个布庄,争那几个铜板!”
颤的声音,像一根残破的蚯蚓,在地面阴暗地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