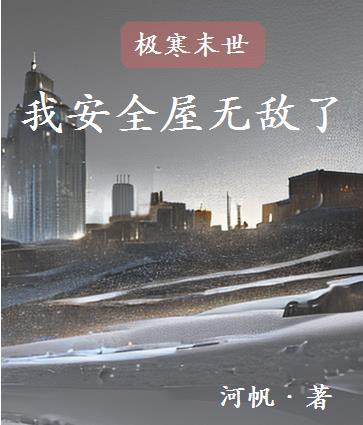爱上中文>谁不说俺家乡美300字三年级下册 > 第十一章 背后真凶(第1页)
第十一章 背后真凶(第1页)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徐老广翘着二郎腿仰躺在自家床上唱曲儿,他手边的小桌上,放着一瓶十几块钱的白酒和一盘吃得只剩下油皮的油炸花生米。
他用手肘撑着床面,另只手倒了杯酒,抿了口,呲牙咧嘴地打了个激灵,又捏了个花生米扔进嘴里。
哼哼啊呀继续唱:“淘尽了……世间事……混作……嗯嗯……滔滔一片潮流……是喜……咿咿……是愁……”
愁字还没憋出嗓子眼,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和咒骂声,“徐小广!徐小广!小鳖孙儿敢坑老子,给我滚出来!徐小广!!”
徐老广腾一下坐起身,赶紧出溜到床边,去找鞋。
可布鞋只趿拉上一只,他家的门就被撞开了。
徐老广的屋里臭烘烘的,徐连山刚进门就被熏得倒退一步,他捂着鼻子,另一只手扇风散味儿,“你屋是猪圈哩!臭哩很!”
徐老广的妻子作势要拦,徐老广掀开布帘从里屋走了出来,“连山,你咋回事,咋进来就吵吵哩!”
“吵吵!我今天要弄死你屋的小鳖孙哩!”
徐连山推开徐老广,掀开门帘朝里一看,现没人后,他又冲到另一间屋。
“你找小广咋哩,他不在家,后晌就出去了。”
徐老广说。
“去哪儿哩?”
徐连山的脸乌青乌青的,身上沾着不少尘土。
“还能去哪儿,这个时候不回,肯定又去镇上的网吧了。”
徐小广自从迷上打游戏之后,经常偷家里的钱去镇上的网吧包夜。徐老广打也打了,骂了骂了,可儿子想玩游戏的瘾只要一犯,就像是吸大烟的人一样,说啥都不管用。
“他哪来的钱去玩?”
徐连山不信。徐老广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一年到头东游西逛,任地荒着也不想着种些粮食。他常年靠救济金过日子,每天盼着节气时政府慰问,要不就是去瞎婶的市赊账,他和儿子徐小广因为钱的事处得很僵,爷俩只要一见面就会闹得鸡飞狗跳,四邻皆知。
徐老广指指徐连山,陪笑说:“你给我哩,忘了?买票……”
“你当我信球!那才几个钱,你屋里的不得再藏几个,不然你吃啥喝啥!”
徐连山把话都说到这儿了,索性一股脑倒出来,“实话跟你说了,我今天弃选,就是你娃给害哩!是你娃用手机录下我买票的视频,又把手机故意塞给福宝哩。要不是我多个心眼从福宝嘴里套出这事是你娃干哩,我这冤屈就白受了!”
啥!
小广!
徐老广瞪大眼睛,惊呆了,“咋……咋还扯上俺娃了,俺娃好着哩!”
“好着哩?”
徐连山冷笑,指着徐老广的妻子,“你问问你屋里的,看你屋的钱少没少。要是没少,你娃去镇上打电脑的钱哪儿来的。还有窝个(那个)手机,咱村会摆置那东西的,只有你娃……”
徐老广扯着妻子进屋,不一会儿他心神不定地出来,“连山……”
“钱莫少吧。我就说,你娃才是真凶!”
徐连山怒火上涌,抄起门口的扫帚就朝堂屋桌子上的摆设砸了过去,徐老广赶紧上前抱着徐连山的腰,“别打,别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