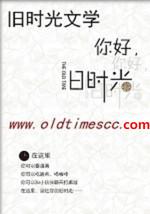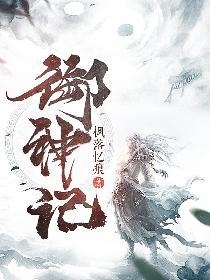爱上中文>流光飞影画集 > 一组画引出一出戏(第1页)
一组画引出一出戏(第1页)
vertical-align:middle;background-image:url(imagespagebreakmiddle。png?t=F0RD)!important;"
>
人物专访
※一组画引出一出戏
——画家应天齐答《南腔北调》记者丹华问
20世纪诞生了两次中国戏曲艺术的“另类”
,一是梅兰芳先生因一幅中国画《天女散花》引发了戏曲创作灵感,诞生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戏曲作品;二是黄梅戏演员韩再芬因看到“西递村系列”
版画而爆发灵感,促进了版画与黄梅戏《徽州女人》的密切关系,并且不是以一幅画去产生戏曲,而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以三十二幅主题绘画作品的形式美感和整体呈现,去影响戏曲的诞生,以一种非常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舞台上作了一次全新的实验与反映。“西递村系列”
版画作者应天齐的答《南腔北调》记者问,较全面地解读了黄梅戏《徽州女人》的艺术内涵与首创意义。
问:《徽州女人》不论是从纯粹审美的意义还是戏曲创作的意义看,都是特别的一种,或可称之为戏曲艺术的“另类”
。从其诞生的过程到舞台上出现的艺术表现状态,都是特殊的和不平常的。
请您评价演员韩再芬因看到“西递村系列”
版画而爆发灵感,以及编剧、导演由此产生一系列戏剧构思的过程。
答:你称这个戏为“另类”
或“特别的一种”
是颇有道理的。韩再芬的突发奇想打破了戏曲诞生的常规,引动一批艺术家对戏曲创新的思考和实践。我以为这种思考和实践的结果
不是属于反叛的,这是由操作模式所决定的。该剧操作模式是个人行为加集团行为。主演韩再芬个人先提出创意并拿出部分资金,然后艺术家自由组合、自定剧本,最后由政府拍板、投资完成。尽管如此,该剧的创作流程却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它是从一组版画的形式美感出发,将其演化为另一种艺术形式——戏曲。有意味的是,这两者颇有些格格不入。前者有着较强的现代意义,属于突破传统版画样式的新版画,而后者较为传统,是独具中国民间乡土味的黄梅戏。这种嫁接就好比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化学元素调配在一起,观察反应结果,调整它们之间的比例,从而产生化合反应,达到和谐统一。其实验性和首创性是以往戏曲创作中没有过的。
在中国戏曲史上,梅兰芳先生以一幅中国画《天女散花》引发了戏曲创作灵感,诞生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戏曲作品,但是他没有将这幅画立在舞台上作视觉呈现,也没有和画家共同研究绘画精神内涵和戏曲精神内涵的关系,因而,画与剧的关系相对没有《徽州女人》来得密切。也许梅先生看到的画仅仅是一个触媒,仅仅是撞击戏曲灵感的燧石。《徽州女人》的创作和前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以一幅画去引发戏曲,而是以三十二幅主题绘画作品的形式美感和整体呈现去影响戏曲的诞生
。孔晓燕在《〈徽州女人〉的艺术创新》一文中谈到了这一不同:“‘西递村系列’版画起着贯穿全篇基调的统摄作用,这些以往只作为舞台背景出现的静态视觉因素在《徽州女人》一剧中从黑沉沉的后台向前台跨迈了一大步。”
note"
src="
m。cmread。wfbrdnewbooks204874591724874oebpschapter02imagesnote。jpg"
data-der-atmosid="
5527c1c8ace2eb92056a5f40f750230621d7e14ab62b"
data-der-srcbackup="
imagesnote。jpg"
>#pageNote#0
从实际生产流程来剖析这一点,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看到其独创意义。首先,是演员在灵感驱动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希望将这一幻想变为现实,版画成了其心仪所在。韩再芬认为这些画作有“极富个性的潜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对生活的诠释,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真的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这个人的痛苦的精神旅程”
note"
src="
m。cmread。wfbrdnewbooks204874591724874oebpschapter02imagesnote。jpg"
data-der-atmosid="
5527c1c8ace2eb92056a5f40f750230621d7e14ab62b"
data-der-srcbackup="
imagesnote。jpg"
>#pageNote#1。这和一般情况下演员被动地接受剧本和角色完全不同。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是属于偶然和罕见的”
。其次,导演(同时也是编剧)也为此种想法所吸引产生了创作冲动,萌发了以版画和自己生活中的奇绝故事为蓝本,从导演构思出发编写剧本的欲望。最后,画家自始自终参与创作(并非漠不关心地将画奉献出来作舞台衬景)。画家产生的创作冲动来源于他的前卫意识。他是将整个舞台表演空间和生产过程作为一种美术行为来实践的,并注重作品的波普效应。于是,创作引发的程序为:演员一画家一导演一编剧。形成剧本的程序为:版画一符合版画意境的最初
导演构思一戏曲故事一剧本。文学剧本的独立意义被打破了,从而受制于创意的前卫意识,受制于版画作品的意境,受制于从版画出发的导演构思。
过去的戏曲创作强调剧本乃一剧之本,注重其文学性、人物个性和戏曲情节的重要性,这本身并没错,但过分地强调却使其偏于一隅,而此事的要义被强调所偷换。这使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一位科班出身的导演。他很喜欢我的画,对该创意却持否定态度,认为黄梅戏和这种现代版画嫁接颇近荒谬。我想请他参加这次探索,他却说:“拿本子来,没剧本不谈。”
相对来看,韩再芬能够有此创意,陈薪伊、曹其敬能够发现这一创意的价值并努力使之变为现实,应当说这种革新意识在中国戏曲界属领先地位,是非常可贵而应加以特别关注和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