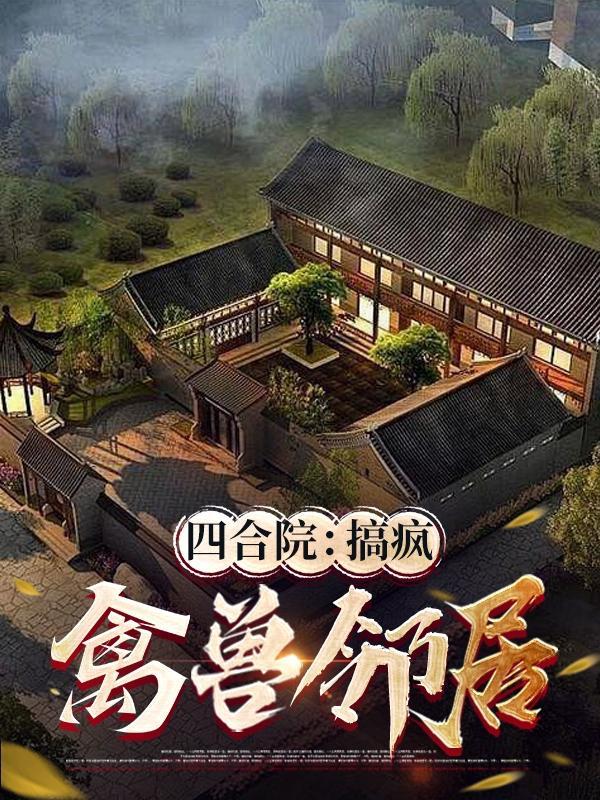爱上中文>流光飞影画集 > 解构两版编辑部的故事(第1页)
解构两版编辑部的故事(第1页)
※解构两版《编辑部的故事》
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有两个版本,分别为1991年版和2013年版,时间跨度22年。其间,邓小平南方谈话,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成为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
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创作的历史背景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改革都未触及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而是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以改善经济效率。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这一改革进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先后放弃了对计划体制的修修补补,转而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原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因而具有了经济转型和过渡的含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轨方式上分道扬镳,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走向激进式转型方式,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知识分子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急需要给自己找到赚钱的路径与理由,1991年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契合了这种社会心态。该剧作为我国情景喜剧的发轫,拓展了我国电视剧的美学品格,其情节发展、戏剧冲突、矛盾激化或幽默抖包袱等多
由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支撑。
两种社会心态的对比
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中人物对话的语言艺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一脸正气的牛大姐,从家到办公室,处处讲原则,满嘴官话、套话,从来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迎合传统主流话语是她的表达方式,因而每时每刻被嘲笑、被解构,简直是传统主流话语的传声筒,自然成为剧中解构的箭靶。葛优饰演的李冬宝则擅长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指点江山的姿态,用高调语气说话掩饰一些无聊、空虚甚至下流的人和事。剧中弥漫的市井江湖习气,彻底消解了过去人们心目中形而上的事物。这种无所谓的心态,自然和人们要放下长期积压形成的心理包袱、大胆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急切心态相吻合。
2013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新编辑部故事》在这种背景下播出。这部新剧剧本有些空洞,不够厚实,剧情浮夸,创作者的心态很难摆脱僵化思想的束缚,导致剧中内容针砭时弊的讽刺力度不够细腻,不敌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那般与现实生活为舞。有评论说剧中“即使是对影星的商业炒作及对选秀节目‘审丑’当道的否定,也基本流于荒诞的嘲讽,空洞无物”
,缺乏实实在在对流行文化的批判,更没有对新的文化建构模式的探索性开拓和
尝试。另外,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中演员隐而不显的表演风格,主要人物幽默辛辣的语言风格,性格各异的人物设置,也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
《新编辑部故事》表演方式的突破
尽管2013年版《新编辑部故事》剧本存在严重不足,但该剧仍以新潮的故事、新老两代演员联袂阵容、新的演绎方式,融入了当代时尚元素,让观众感受到了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欣赏到了它对1991年版的承继与弘扬。其中一大亮点是贴近舞台剧,即打破“第四堵墙”
的表演方式,这种电视剧+舞台剧的表演方式,在国内影视剧中尚属先锋之举。虽然这种表演方式有些夸张,但对电视剧表演来说,是一种创新,跳出了电视剧长期以来固定的表演模式和风格,为我国电视剧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第四堵墙”
原本是戏剧术语,大意是说我们在看话剧的时候,一般舞台有三堵墙,但演员和观众之间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即沿台口的一面不存在的墙,演员表演时,完全沉浸在人物角色的世界中,“第四堵墙”
的作用是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而只在想象中承认“第四堵墙”
的存在。
《新编辑部故事》中,主演经常会演着演着突然盯着镜头,来一段内心独白,并试图用眼神与观众交流,
这种表演方式很容易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从而避免观众跳戏。导演郑晓龙受访时坦承自己就是想突破传统有所创新,而“大众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也总要有个过程”
note"
src="
m。cmread。wfbrdnewbooks204874591724874oebpschapter10imagesnote。jpg"
data-der-atmosid="
5527c1c8a6e2eb92056a5f409e59ed0621d7e15aa0b8"
data-der-srcbackup="
imagesnote。jpg"
>#pageNote#0。
缺乏苏轼式的自嘲精神
解读《新编辑部故事》反映的时代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回溯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自称“民间知识分子”
的王朔与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人文主义”
的争论。被讨伐为“痞子作家”
的王朔,以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时代特质的精准把握,用社会批判意识方式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三十年后解读《编辑部的故事》和王朔的语言风格,可发现其审美核心是:语言的活跃是思想解放的反映,语言从官话、套话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编辑部的故事》摆脱了思想僵化的束缚。因此,《编辑部的故事》以通俗、诙谐、狂欢的语言风格,影响深远,甚至塑造了一代人的语言风格:自我贬抑、调侃、反讽、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完成了20世纪90年代一代人超越现实的精神放飞。
《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后,有一个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中冯巩问:“冬宝,想啥呢?”
葛优答:“想戈玲呢。”
冯巩拿出一根火腿肠给葛优,镜头
一转又问:“还想戈玲吗?”
葛优翻着白眼问:“戈玲是谁?”
学者郭松民分析说:“这个广告真可以说是《编缉部的故事》剧微续集,它用直截了当的对白诠释了‘有奶便是娘’的亘古真理,明示一切超越口腹之欲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这种理直气壮深得初涉市场经济大潮、沉浸在发财梦想中的国人之心,这让他们免于心理纠结,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实际上,《编缉部的故事》剧当时的大红特红,正是和它这种解构传统以及宏大话语,让一切追逐私利的行为都正当起来的功效密切相关。”
《新编辑部故事》的导演郑晓龙曾抱怨做喜剧禁忌太多。笔者以为,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创作者和观众都缺乏苏轼式的自嘲精神——怀着无比开朗豁达的心态,以自嘲和微笑消解生活的苦难,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因此,《新编辑部故事》针砭时弊的力道少了很多。
两版《编辑部的故事》人物没有主心骨
无论是《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戈玲、李冬宝、余得利、牛大姐,还是《新编辑部故事》中的安红、袁帅、何澈澈、李童宝,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既自负又自卑,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总是间歇性地斗志昂扬,持续性地萎靡不振,干什么都没有内在动力,明知道这样做不对却又忍不住享受颓废带来的无压力感,就这样浑浑
噩噩到了剧终。这是两版《编辑部的故事》塑造人物方面存在的最大缺陷。剧中人物没有主心骨,即使外表再华丽,也永远无法肩负使命、负重前行。两版《编辑部的故事》都没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待下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