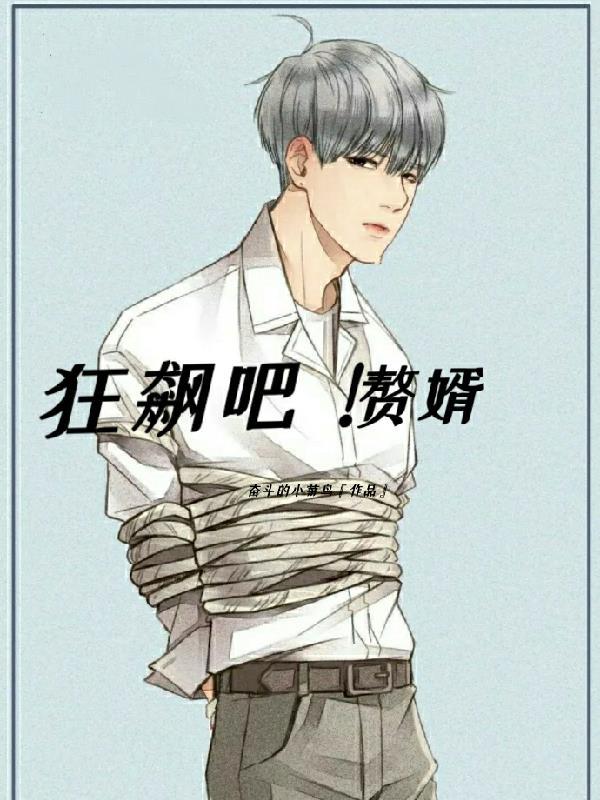爱上中文>四爷后院当咸鱼(清穿)_第54节_久久网手机版 > 第7章(第2页)
第7章(第2页)
果然如此,馨瑶在心里一叹。
这时大黄耳朵一动,说:“汪,有人来了。”
馨瑶赶紧把铜壶重新包起来,对大黄说:“这个东西暂时借我一用,不要被老何头发现了。”
她把小包袱笼在自己的大宽袖里,然后顺着刚刚的路,从另一边溜到门口,扶着墙,一副虚弱的样子。
白鹭吓得眼眶都红了,颤着手过来扶馨瑶,嘴唇抖着说话都发飘:“格格你可让人担心死了,咱们把前院都快翻遍了,要是……要是……”
要是真的被伤到,身上留了疤痕可怎么好!
馨瑶也有点过意不去,踱步慢慢走回自己的西后院。一路上思量着这件事,心情沉重。
挽马平日里只接触马棚的马奴和车夫,再不然就是拉车拉货,这铜壶不是谁拿着喝水就是放在马车里,才能被大挽马见到。
想到这里,馨瑶只觉得后背一阵阵的发冷。
若是老何头的壶,他用不着半夜心虚的埋起来,所以那该是陈老头的东西才对。
陈老头挪出去后,按说他的东西都应该烧掉,扔掉才对。老何头却匿下了陈老头这个伤寒病人经常用的茶壶,换到马车上给弘晖阿哥用了。
弘晖本就刚种痘身体虚弱,免疫力低下,根本扛不住这种细菌病毒感染。事后因铜壶不能烧掉毁尸灭迹,只好偷偷埋到自己熟悉的马棚里,发了一笔横财!
真真是好歹毒的心思!
回到自己的西后院,馨瑶坐在那里发呆了一下午,似乎是把能想起来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想,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
想起自己用帕子拿过那铜壶,她叫来白鹭,拿出中午用过的手帕,道:“拿火盆来。”
“格格?”
“无事,”
馨瑶显出浅浅的笑意,安抚她,“中午被撵到马棚跌了一跤,用这帕子垫着,谁知道沾了什么东西,我心里不爽,不如烧了了事。”
白鹭听罢,以为格格是觉得中午之事过于丢脸,迁怒到手帕上,是以亲自拿着火盆来烧掉,馨瑶看着那张狂飞舞的火舌,一阵恍惚。
馨瑶有些后悔一时冲动把铜壶拿回来,现在倒成了一件烫手山芋。
这件事她自己肯定是不能出面的,还是要想办法扔给正院,福晋是弘晖的亲娘,应该能查出去个结果吧?
正好晚上小珍珠又来找她,馨瑶就跟她说:“小珍珠,我帮我一个忙呗,这个小包袱,你明天给带到福晋院子里,最好在正屋门口弄出点声响。”
“喵——我知道了!”
给钮祜禄格格送冰镇西瓜……
第二日一早便起了风,密密的云层挡住了万丈光辉,小珍珠按照馨瑶昨日说的,滚着小包袱来到正屋附近,正对着西稍间卧室的窗下。
滚了这一路小包袱有些松散,小铜壶的壶盖和壶身分离,发出丁铃当啷的响声,在这个院子里格外刺耳。
福晋乌拉那拉氏出生于康熙二十年,比四贝勒小三岁,为人有些古板,平日里极重规矩,因此这正院的氛围也是十分肃静。更何况现在福晋病重,熬不熬得过去还是两说,是以这正院的下人们更是恨不得揣着脑袋办差,就怕一个小心填了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