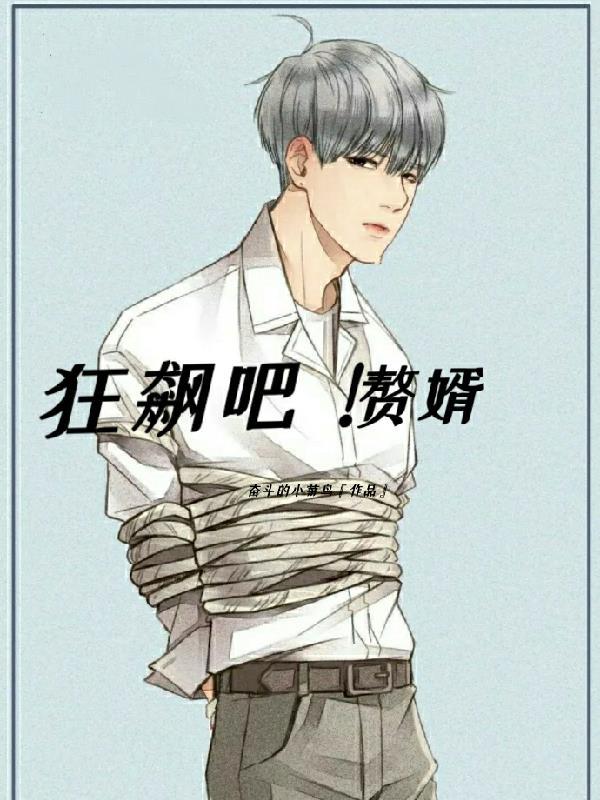爱上中文>画耳朵照川明 > 第61章(第2页)
第61章(第2页)
可它抱的是姜早几个小时的心血。
姜早的手霎时收紧,抓着何斯屿的肉,“别动我的画!”
指甲猛地按压布料,陷入他的肉,虽然没感觉到出血,但痛觉神经还是敏锐的感知到,何斯屿“嘶”
了声,一转头就看到姜早整张脸都紧张的皱起来,眼里是一阵忽明忽暗的星光。
这画对她这么重要?
重要到害怕失去?
何斯屿抬手揉了揉姜早的头发,动作一改平常的温柔,像是在安慰小朋友,甚至比安慰言朝生时还要温柔。
他没说一句话,抬脚往一旁跨一大步,捞起地上的床单,目光斜视着抱着画摇摇晃晃的猴子,找准时机就扑上去。
杀意在房间里波动,猴子多危险也有所预知,一个侧身,“呀!”
了声,一手拿着画框,一只手胡乱抓向何斯屿。
何斯屿的手臂上愕然破了一个洞,片刻,他的纯白衣服就被血染上红色。
何斯屿没想到猴子的爪子这么锋利,倒吸一口气,沉着脸转身,一撑床单,杀气从他的眼睛溢出,姜早捡起地上的睡衣,也向前帮忙。
窗外的月光倾泻下来,将何斯屿和姜早的身影找的很高很大,猴子被人类驯服过,此刻在它眼里他们已经变成了凶猛的马戏团团长和拿着鞭子的训员,瞬间软了下来,瑟瑟发抖地看着姜早。
何斯屿仰着嘴,扬起床单将猴子盖住,尔后又从客厅找来一根麻绳,把它绑在桌子角,过程中他的后背又被抓破一个洞。
“好了,给马戏团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拿吧。”
弄完这些,他拍了拍手,站起身看向身后,却见姜早闷闷不乐地盯着手中的画看。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还是被弄坏了。”
何斯屿走到她身边,低头看向那幅画,端详良久都没看出这幅画哪里坏了,反倒意外的看懂了这幅画的意境。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
他问道。
姜早:??“笼中的白天鹅。”
言毕,何斯屿皱起眉,他自小做古诗鉴赏就以自我感觉为主,所以即便作者就在身边,他还是要将心中的答案说出来。
“在我看来,它更像是白天鹅的自我救赎。”
他说的有理有据,“虽然它身处笼子,但是铁门是半开的,缠着铁龙底下的海藻也被一刀砍断,所以只要这只白天鹅撑开翅膀,沆瀣一气就能撞开门飞出去,即便撞不开门也能把笼子撞倒,不管怎样它都能得到自由。”
姜早听着他的话,又仔细的观察面前的画,因为猴子的那一爪子,缠着笼子的深色海藻被一刀切露出画框的白,最让她意外的是,她居然鬼使神差地把渐渐关上的笼门画成了正要打开的门。
原来在她心里有些东西正在慢慢的改变。
“它又飞不远,逃出牢笼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不知是在问一旁的何斯屿,还是在问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