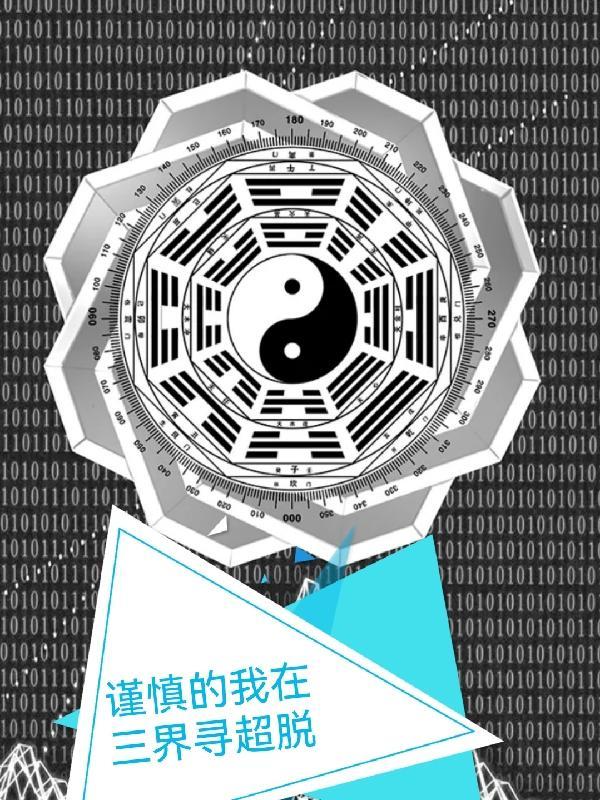爱上中文>雨溺殊晚全文免费 > 泪痣(第2页)
泪痣(第2页)
她在原地站了会儿,拿出手机给钱舒荣了条消息报平安。
妈妈,我到了。
等了好久还没看见回信,祁安看了下时间,有些晚,怕收拾不完,便放下手机摊开行李箱。
她带过来的东西并不多,也没什么好整理的。
只是房间里灰尘很重,杂物也多,清理起来实在是个大工程。
书桌衣柜上的积灰被擦净,搁在一旁的手机亮了下,祁安擦干手拿起,屏幕上却只有一条浏览器推送。
聊天框依旧空荡荡的。
钱舒荣没回。
本以为是她在忙,可不经意点开朋友圈,现就在十分钟前,她还分享了一张图片。
看起来是在某个高档酒店享用晚餐。
大概是舟车过于劳顿,叫人精神脆弱,又或许这寂静的夜太像温床,滋生着情绪疯涨。
被告知转学的那天她没哭,真正离开临舟的时候她也没哭,但就在这一刻,那张照片就像是银针一样,在心口的位置戳破一个小口,委屈如洪水般涌了出来,滚烫的眼泪氤在眼眶。
肩膀仿佛被压上了千斤的重量,祁安承受不住地弓起身子,最后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纤细的双臂环住膝盖,脸埋在臂弯里,后背两块蝴蝶骨凸起,肩膀小幅度地抖,唇肉被咬到紫。
祁安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从她有记忆开始,妈妈就对自己非常冷淡。
那个时候爸爸和弟弟都还没有出事,他们也曾是其他人眼中羡慕的美满家庭,只有妈妈,她很少笑,也很少和自己亲近。
最开始爸爸还会耐心地开导她,说妈妈就是这种性格,她也一直相信,妈妈是爱自己的。
可她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抛弃自己
房间里的温度很低,祁安后知后觉感受到攀上胳膊的冷意,顺着毛孔和血管,钻进她的身体里。
长有些凌乱地被泪水糊在脸上,眼尾委屈的那抹红色迟迟不肯散去。
“咚”
一声,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口袋里掉出来,砸在地板上。
是一个兔子模样的针织钥匙扣。
钥匙扣的做工很粗糙,针脚很粗,眼睛也歪了一个,但祁安还是马上伸手捡起,将沾在上面的灰尘轻轻擦掉,然后紧紧攥在掌心里。
难过好久也没能被消化,直到小腿麻,祁安才踉踉跄跄地站起。
晚上十一点,她终于收拾完所有东西。
外面的雨渐渐变大,小房间内更加潮湿,浓重的霉味呛得人难受,风雨交杂拍在窗户上,出有些可怖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把玻璃敲碎。
房间的隔音有些差,不知道周围哪户人家在吵架,争吵声与打骂声纠缠在一起,源源不断地撞进耳朵里。
祁安躺在床上,盯着陈旧斑驳的天花板,四肢酸痛得像是被拆卸过,明明累得不剩一点力气,但她怎么都睡不着。
这黑夜,可真漫长。
第二天还是阴天。
外面的雨终于停了,但房间里仍是昏暗一片。
祁安有些疲惫地睁开眼,拿过枕边的手机看了下时间。
早上七点。
其实这一夜她根本没怎么睡着。
邻居家一直在吵,她这个人睡眠质量本身就差,哪怕是一星半点声音也能惊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哭了一场,眼皮沉沉的不太舒服,祁安多躺了半个小时才起床。
她随便洗漱了下,然后拿着钥匙出门。
这一带附近都是老旧的居民楼,灰黑色石墙上爬满藤蔓,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花花绿绿,小贩们推着快散架的三轮车奔走叫卖在小巷里。
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食物香气,祁安后知后觉有些饿,随便在路边找了个早餐店,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白粥。
她吃饭的时候很安静,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喝着粥,热气在她纤长的眼睫上氲出淡淡一层雾气。
从早餐店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天晴了一点。
昨晚收拾房间的时候她留意过,里面很多东西已经没法用了,都要重新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