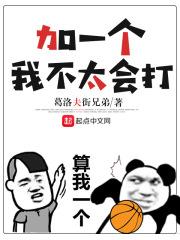爱上中文>雨溺讲的什么 > 第 97 章 肋骨(第4页)
第 97 章 肋骨(第4页)
掌心按上小腹那块,平坦中被攻占出凸起轮廓,他夸奖她说好厉害,又哄着她不要忍,哄她叫出来。
他在她耳边说了好多句爱。
闹到快要天明,陈泽野帮她洗澡,帮她把身上的水痕擦干,最后抱人回到卧室里面。
整晚情绪消耗太多,祁安其实很累,但是她却不肯睡,蜷缩窝在陈泽野怀里,指腹蹭着他胸口那处纹身。
嗓音哭到哑,她轻轻叫他名字“阿泽。”
陈泽野手心很暖,贴在脊背那里,回应着说我在。
祁安仰起脸去看他“分开这几年,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陈泽野沉默了很久,看着她微湿的双眼,似乎明白逃不开,还是不确定地问“真的要听吗”
“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讲的。”
他自顾自地笑起来,“就是怕你会哭。”
当年6睿诚意外死亡,陈泽野被牵连诬陷入狱,虽然最后法院判定无罪,还给他该有的清白,但还是被有心人拿来扩散酵。
流言蜚语面前没人会在乎真相,某些罪名一旦扣上便很难摘掉,雪崩之时没有一粒雪花真的无辜。
陈绍商作为他的父亲,同样被卷入风波之中,商人之间的争斗本就暗流涌动,多年来在外塑造的形象遭到质疑,他因此失去了一笔很重要的生意。
之前他把陈泽野送到黎北,就是想远离这个累赘,没想到会再次闹出这种事,一气之下决定再次转移。
陈绍商找来那帮人其实很废物,算不上是陈泽野的对手,但他铁了心要把人带走,不惜一切代价,最后强行注射了镇定麻醉类药物。
剂量很大,打斗过程中又受了伤,陈泽野在高烧中昏迷了
三天才醒。
陈绍商甚至没给他回临舟的机会,直接将人送到一个叫做兴怀的县城,那里比黎北更加偏僻,更加荒凉。
他砸碎陈泽野的电话,隔绝他与外界的所有往来,又收走沈初宜留给他的全部财产。
陈泽野被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房间中,里面没有窗户,见不到阳光,分不清日与夜的界限,时间更是混沌失去概念。
空间很小,设施只有一张板床,角落里还装有大量监控摄像头。
长久的不见天日中,潮湿霉气就像是食人兽,一点一点吞噬着他的生命。
陈泽野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平常到好像故事的主人公根本不是他,只是在转述其他人的经历。
可祁安眼泪掉得很凶,怎么擦都擦不完那种。
陈泽野最见不得她哭,心脏跟着抽痛,揉了揉她红的眼尾,低下头靠近哄着“别哭啊宝贝。”
“那后来呢”
祁安眼睫毛上挂着湿漉漉的水痕,声音也泛起潮湿“你还回过黎北吗”
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回答,陈泽野脊背僵愣片刻,手上动作也停顿,喉结轻轻颤动起来。
他声音好沉,呼吸也是“回来过。”
陈绍商了他整整半年,十二月的时候,将他送到当地一所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学校。
说是学校,其实和监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校园四周的围墙都有加固,外面还缠着重重叠叠的铁丝网。
学校里面的招收对象都是有问题的青少年人,包括早恋、厌学、打架、叛逆等等,对外宣传很好,让人足以心动,实际里面却充斥着各种残暴与虐待。
兴怀的冬天远比黎北更加难熬,温度直逼零下二十度,暴雪一场跟着一场。
那种冷是具象化的,空气中涌动的白雾,窗户上凝结的冰花,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冻结淹没。
太阳东升西落,日历不断撕开新的一页,12月31日,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也是祁安的十八岁生日。
学校最北侧围墙有一处很隐蔽的坍塌,并且是监控死角,平时路过的人少之又少,陈泽野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决定从那里逃出去。
似乎天公都在帮他,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跑到车站买了回到黎北的火车票。
那五个小时的车程,他全部用来紧张焦虑。
他脑袋里面想了很多,想祁安今晚可能在哪,想该怎样才能找到她,想见面后该怎么和她解释,又想如果她生气了不肯理自己该怎么办。
晚上七点,火车抵达黎北。
离开半年,这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颓坯陈旧的矮楼,痕迹斑驳的石墙,街道两旁挂着大红色灯笼,偶尔遇见往来行人,裹着外套脚步匆匆。
陈泽野先是去了明椿巷,137号大门紧闭,里面并没有人在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