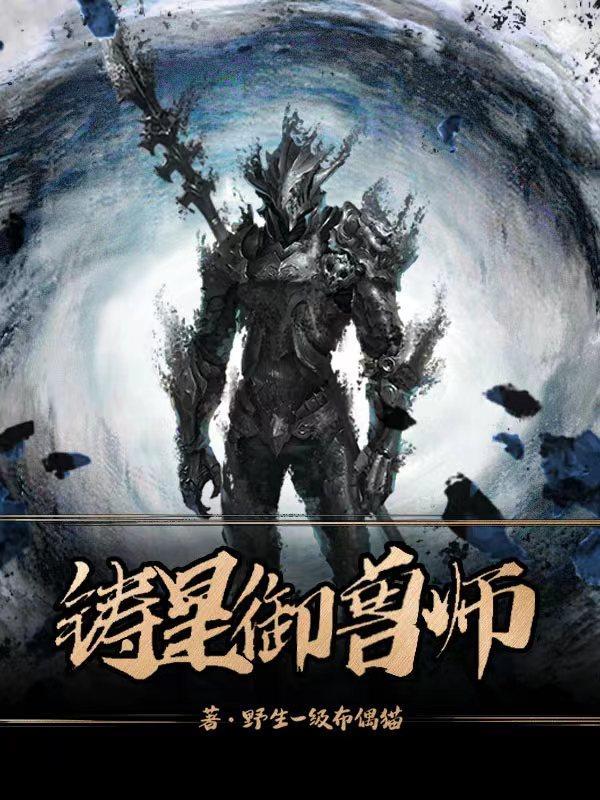爱上中文>盐碱地适合种什么农作物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散会後,蒋芸在大门口堵辛梁星,拉着他好说歹说终於把人拽去了电影院。这个电影已经上映很久了,很是卖座,辛梁星没那个艺术细胞,坐在黑白荧幕下,打了一晚上的瞌睡。
电影散场,蒋芸意犹未尽,对着辛梁星说个不停,辛梁星都只是敷衍的嗯。
影院门口的彩灯闪烁,映得地面一片斑斓,蒋芸站在灯下,问:「辛梁星,咱俩好,行不行?」
辛梁星浓浓的睫毛扇开红光,瞳膜光影交织,恰似多情又无情的缓缓摇头,拒绝说:「不行。」
蒋芸好像很喜欢他,从他进这个厂子就一直在追他了,辛梁星很费解,他明明已经拒绝过无数次了,蒋芸还是要跟他告白。如果是做朋友,他并不介意,可多了层男女关系,他怎麽也接受不了。
蒋芸伤着心了,使脾气道:「不行就算了。」她跑开,拒绝辛梁星送她回家。
她一离开,辛梁星就看见街拐角的白砚了,好奇怪,哪里都有他,辛梁星扫他一眼,径直转身离去。
白砚在昏暗的角落承着辛梁星朝他瞥过来的冷漠视线,薄後适中的唇翕张,舌根发紧,徒然望着他走远。
电影院还在放映,白砚从售票员那里买了张票,自己坐在视野正好的放映厅中央,任黑白画面扑进他眼球。平淡的开场,白砚端坐着,直到男女主亲吻,他才猛然间抓上膝盖,上下牙齿咬合,身体微微前倾,辛梁星有没有在这一片黑暗当中亲蒋芸啊?亲她的脸还是亲她的嘴啊?白砚抓的膝盖生疼,乱糟糟的思绪比映画还要跌宕起伏。
周六,辛梁星没有活动,躺在床上太煞时光,於是又提起鱼竿去河边钓鱼。
天愈发热了,他戴着草帽,卷起一截袖子,露出结实的小臂,太阳把那节手臂照出古铜色,虬结的青筋在手背蜿蜒,他眯了眯眼,有些燥。
不会钓鱼,他鱼竿买了有俩月了,一条鱼也没钓上来,要不找个老头请教请教算了。他从兜里摸了根烟,划开火柴,嘬了口菸嘴,在一片吞云吐雾中舒展开眉头。
第6章吸一口
好些老头都去下象棋了,钓鱼的人也没那麽多,辛梁星仰躺在地上,身下是乾燥的泥土和零星几株野草,薰风自南边儿刮过来,荡平河面再回旋,风中带着水腥味儿,又凉丝丝的。草帽盖在脸上,阳光穿透席草编织的缝隙,洒落下细碎的十字光斑。
辛梁星眯了眯眼,透过草帽看向那影影绰绰的寸方天地,想不远处的这条河,想他还没摸熟的饵线,想他快抽完的菸丝,想下一次集会是什麽时候。
他是在工作後开始抽菸的,旧报纸卷菸丝,火柴一划,尼古丁的味道从鼻腔到肺腑流窜,被麻痹的神经驱使大脑皮层兴奋,放空,什麽鸡零狗碎都随烟圈儿散出去,缭绕着在四野中消失殆尽。
下次集会还远,他摩挲着拇指,拿下草帽,从地上跃起,借着精壮的腰力,起的利索。他拍了拍背後的土,收起鱼竿拎起马扎,朝镇里走去。
供销社建在马路口,四通八达,穿个街都能看见那青瓦下气派的门楼,朱红笔勾出磅礴的字样,大敞的前门和後门来往着熙攘的身影。
辛梁星进供销社的时候,白砚正在打算盘,噼里啪啦的珠算声比炮仗都热闹。
他看白砚上下曲弹的手,乾净,指甲缝里没有灰,极是文静的一双手。
白砚在一团阴影中抬起了头,猝不及防的望见辛梁星,他好像刚从外头回来,发际冒出汗珠,晶莹的挂着。辛梁星一手放在柜台,漫不经心的扫过橱窗,问:「菸丝有吗?」
隔着个柜台,站的有些近,细嗅能嗅到他身上被蒸腾过的肥皂味,纠着浅浅的咸汗,白砚勾头,轻轻吸气,话音飘忽着说:「有。」
铜造的簸箕铲过菸丝,秤杆翘高,辛梁星看见他拨秤砣,拨到不听话的秤杆在他手中服帖,「要多少?」他问。
「三两。」
白砚招呼他过来看秤,辛梁星摇摇头,说:「你看就行了。」
没来由的信任,也不是不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别人来都是把秤盯死了,少有他这种不把买卖当回事儿的人。白砚不会少他的,更不会多他的,公家的东西,该怎麽就是怎麽。
白砚用油纸把菸丝包的四四方方,细麻绳捆着递给辛梁星,辛梁星搁下钱,抄起鱼竿,迎面走入春日中。
到了晚间,温度降下来,辛梁星坐在屋顶,看深蓝天幕上渐渐闪亮的星星,猩红的菸头在暮色中忽明忽暗。还没彻底黑透,他眺向远处,能看见香樟树巨大的树冠,像坠落的一团云,又像半截孤山。
斯斯文文的敲门声骤然响起,辛梁星咬着菸嘴含糊不清的问:「谁啊?」
「我…白砚。」回话的声音小,怕被听去,又怕辛梁星听不到,固执的强调道:「是我。」
辛梁星爬下屋顶,趿着布鞋,去给他开门。双扇门只开了一扇,辛梁星立着,头顶快接近门框了,嘴里还叼着烟,不让他进来,问:「有事?」
白砚递上一包菸丝,说话声音极小,在徐徐的夜风中显得雌雄莫辨,「给你。」
「不要。」辛梁星拒绝的果断,非亲非故,他可不图那点小恩小惠。
白砚睁大眼睛看他,门口的灯没开,只能看见大致轮廓,浓稠的影儿,黢黑炯亮的眼神,和斜在嘴角的烟,忽闪忽闪。
「你要吧,行吗?」白砚有点像是哀求他。
辛梁星油盐不进道:「不要,拿回去你自己抽。」
「我不会。」白砚坦言,他不抽菸的,菸酒都不是什麽好东西,他不沾。
辛梁星歪了歪头,动作轻微,不很明显。他拿下烟,冲着那张发白的脸,淡淡吐息,薄薄的一层烟圈儿,比迎面喷薄而出的浓呛烟味儿还要食髓知味。白砚低咳,想後退一步,却被他按住後脑勺,一手自白砚嘴角勾着,顺着唇缝,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半截烟喂到了白砚嘴里。
白砚怔住,嘴巴沾着那节被辛梁星唾液濡湿的菸嘴,偏软,噙着像是要化在自己嘴里。
该吐的,舌尖抵着,推就着,菸嘴更湿了。却没从他嘴中退出半分。
辛梁星的嗓音像榆钱儿轻响似的,暧昧的,擦过白砚耳畔,「吸一口,吸到肺里。」
白砚笨拙的,吸进一口火辣的气体,穿过喉管,穿过鼻腔,像有一条火,在他的感官中奔袭,灼烧。他咳出撕心裂肺的声音,咳弯了腰,咳掉了那截菸头。橘红的光点落地,渐渐堙灭在黑暗之中,他觉得可惜。
辛梁星嗤笑他的窘态,边用宽厚的手掌拍在他瘦弱的背脊,玩笑道:「怎麽那麽笨?」
手茧削去部分触觉,他下手向来没轻没重,白砚被他拍的後背又疼又麻,呆滞的,屏息去感觉脊骨的那团火热。辛梁星的掌心滚烫,哪怕是捉弄,也带着燎人的温度。
「我…不笨。」白砚把菸丝塞进他怀里,飞也似的跑了。
第7章下雨天
稿纸被裁的方正,辛梁星往上头抖落菸丝,他卷的是白砚送过来那包,不是供销社卖的那种大批次的劣质菸草,而是醇浓的,上了好几个档次的菸丝。真舍得送,辛梁星划开火柴,在一片烟雾中想到白砚落荒而逃的背影,像只燕子,不着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