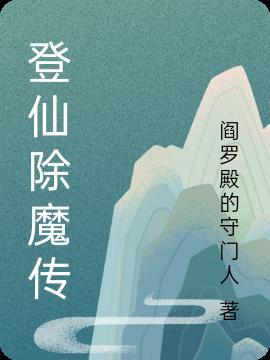爱上中文>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上一句是什么 > 第60章(第3页)
第60章(第3页)
按照律法,他早就应该在婉娘事时就遭千刀万剐。可惜当时让他逃过了一劫,不想连十多年前的大案,他也牵涉其中。
数十万两银钱不知去向,还能有什么可能?必是被贪污了!
“可是张文思区区一届县丞,怎么敢?”
“若是只他一人,未必能撼动文石。”
“你的意思是……”
吴寅不敢想了。
他浑身血液都在沸腾,叫嚣着让他赶紧做些什么。他想到还滞留此地的妹妹吴嘉,更是抓心挠肺,恨不得立刻把人送回京城去。
自打来了此地上任,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就没消停过。
哪个地界像景德镇这样闹腾的?
此时此刻,徐稚柳的心情不比吴寅平静。若当真只是关系到万寿瓷,关系到民窑生死,毕竟明年才是万寿年,眼下搭烧才刚刚开始,一切都有回旋的余地。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没有告诉吴寅的是,他的父亲也死在文定窑出事的那一年,和文石投河自尽的时间只相隔了一个月。
虽则一个生在瑶里,一个在景德镇,两地相隔百里,也不会那么巧合,但他就是有一种预感,一种说不出的诡异的预感。
他父亲的死,和文石有关。
**
接下来的日子,徐稚柳一直尝试接触四六。
县衙里的户籍文书并不完整,文定窑的相关文书也遭了焚毁,在吴寅多次探访不得后,徐稚柳越肯定文定窑和文石的背后,隐藏着滔天的秘密。
如今文书资料都遭到了有心人的刻意损坏,唯有找到文石本人,才有可能获悉真相。可惜,文石亦或是四六,大约不想被人现真实身份,多年以来深居简出,吃住都在账房里。
王瑜名下瓷行、商铺的管事们若遇见紧急情况,需要用到银钱,都得亲自去安庆窑汇报。逢年节、月季度的正常结算,也都是一起去主家,同时向账房先生和大东家做汇报。
安庆窑这档子规矩,在遇见突情况时委实有些麻烦,但王瑜仰仗四六,也不勉强,好在多年以来,四六主持得当,安庆窑蒸蒸日上,如此规矩也就延续了下来。
徐稚柳想过闹出点动静引蛇出洞,只怕是以文石的性子,就算出了门,前簇后拥的必不可能只他一人。
吴寅倒是说过,可以潜入安庆窑把人抓出来,但这么一来,未免动静太大。
最重要的是,文石既送了信来,想必不会毫不提防。这时候他们有任何举动,文石都会比往日更加小心谨慎,是以,想单独和他见上一面,除非他自己露脸,否则难于登天。
“这可怎么办?”
连绝世高手吴寅都犯了难。眼瞅着马上入冬,翻过年就是万寿,日子越近,他就越是紧张,偏偏吴嘉还是头倔驴,他好说歹说也没能劝动她回去,一而再的反倒引起她怀疑。
这几日吴寅当真是茶饭不思,人都瘦了一圈。
他像个无头苍蝇在书房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忽而,他听到窗边的人开了口:“上次你不是问我,王云仙买马意图为何?”
“啊?”
吴寅想说,敢情你听到我说话了呀,怎装聋子装得那么像!
“他不是为了给踏雪找老婆。”
“那是为了什么?”
徐稚柳望向远处,目光悠远。
秋风吹动他的衣袂,水青色的波纹将他带回那一亩方塘间。想到那日被他随手扔在积水洼的《横渠语录》,他声线有些粗哑。
“为了哄她高兴。”
“明日是她的生辰。”
“我想去湖田窑,亲口和她说一句生辰快乐,百岁长安。”
这或许,是他能对她说的最后一句祝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