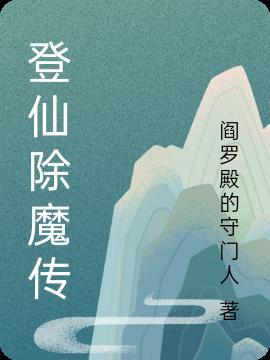爱上中文>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下一句是什么 > 第27章(第3页)
第27章(第3页)
这条集市逐渐扩大,日以规模化,到了如今从手绘的地图上看去,沿着五龙山南下,经薛家坞、药王庙,绕珠山东侧,直到青峰岭脚下,以御窑厂为中心,周边形成包围之势。
民窑林立,一幢一幢地穿插其中,铺平街市弄堂——一个沿河条形的格局,从此被拉伸突破,变成了一条向东探头探脑的春蚕。
夜色中去看,这条春蚕耸动着胖乎乎的身躯,额角冒出长虚,向着光亮的地方,努力抬高灿灿的眼眸。
徐稚柳每每巡窑,并不只是绕着湖田窑一带走,而是将御窑厂沿河而立的周边都走一圈,看一看深夜的窑火,审一审心底的良知。
数年过去,初心未改,如此也该将归期提上日程了。
就在他走后不久,仅仅一墙之隔的安庆窑内,工人小厮们都已熟睡,然主家厅堂里仍旧灯火通明。
王云仙自知犯了错,回到家自觉向王瑜请罪。王瑜不比徐忠,再怎么保养得宜,也是个近六旬的小老头。听完王云仙的叙述,脚底不住颤,人一晃荡,险些倒下。
亏得梁佩秋就在身旁,一手扶着王瑜坐下,一手倒了茶来。
回来的路上,梁佩秋已经迅有了章程,她先在马车上匆匆脱掉婉娘的襦裙,改过髻,拜托时年将婉娘衣服烧毁,之后在门房处换了小厮的衣裳,一番敲打令他们管住嘴巴。
进入主屋后,屏退众人,容王云仙一人进去。
父子俩没说两句话就吵了起来,尔后王瑜拧着王云仙的耳朵破口大骂,王云仙嗷嗷直叫,梁佩秋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进去。
由她半述了一段,王云仙补了一段,两人磕磕巴巴讲完始末,都老老实实地跪了下来。
王瑜叫梁佩秋起来,她先还不肯,直到王瑜高声斥她不听话,她怕小老头气晕过去,忙跑到旁边伺候。
故才能适时地搭把手,扶住小老头。
王瑜坐了好一会儿,胸口的郁气仍不得缓解。
梁佩秋奉茶过来,他也不想喝,一双沧桑的眼眸死死盯着面前的不孝子。
良久,他道:“你还记得你兄长吗?”
王云仙声如蚊蝇:“记得。”
“记得?你记得还敢狎妓?!”
“我没有!我是被陷害的!”
他忙把头摇成拨浪鼓,求救似的看向梁佩秋,希望她能帮自己解释。
由眼下情况来看,他和婉娘那一夜很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生,只是婉娘演的一场戏罢了。
梁佩秋刚想开口,就被王瑜打断。
“你不用帮他开脱,若非他去了那等寻花问柳之地,怎会遭人陷害?若非其身不正,怎会掉入贼人陷阱?张文思是何许人也,我没有提醒过你吗?”
王瑜猛拍桌子:“王云仙,那日你随我一道去县衙送礼,离开时我是如何同你说的?你且一字字道来!”
王云仙本想装死糊弄过去,不想被老爹当场点名。
碍着梁佩秋在场,他实在不想回忆那天的情形,可他即便不抬头,也能感受到一道火辣辣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他。
他硬着头皮道:“杨公在位多年,没收过底下百姓一棵菜,这位新县令刚上任,我王家窑的私库里就痛失两件宝贝,实在可恨!比那太监还要可恨!你且记住,以后不论在哪儿,都离这位张大人远点,别叫他再拔去一根毛!”
王瑜见他复述得一字不落,气得火冒金星:“你明知那厮不是个好东西,还送上门去被骗,王云仙,你脑袋长屁股上了?”
王云仙委屈。
“我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只是为美色所惑,慷慨解囊一回,就真把自己当成了大侠?人家夸你两句你就翘尾巴,你怎么那么轻贱!”
“师父!”
梁佩秋及时打断王瑜,不让他再说下去。
眼瞅着王云仙没了方才的生气,蔫了吧唧缩成一团,梁佩秋替王瑜找补:“师父,小心气大伤身,您且喝口茶缓缓。”
她又对王云仙道,“师父这把年纪了,瞧你把他气得,话都说不直溜了,还不快好好认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