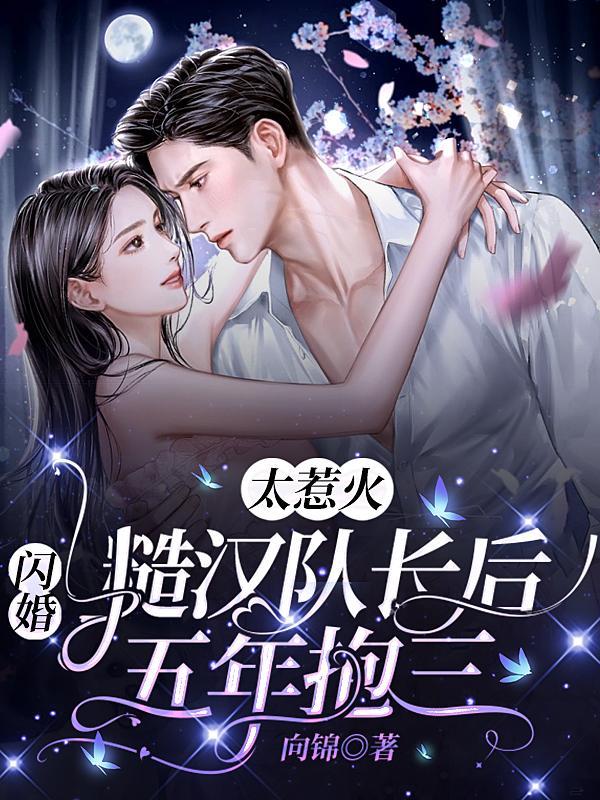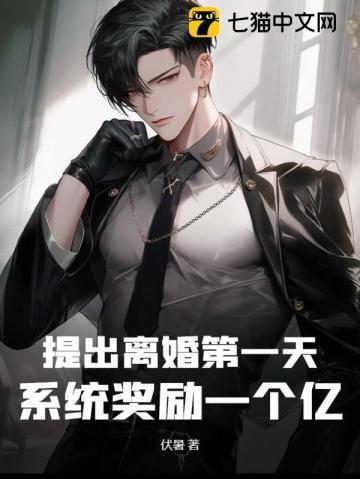爱上中文>沟头堡的风华雪月 > 3暗流涌动(第1页)
3暗流涌动(第1页)
肉香四溢时,时间就到了晌午。
菜往桌子上一摆,这一大家子人(杨廷松老两口、杨伟一家,杨刚一家、除了二儿子杨书勤)就围聚在了一处。
等周末差不多就该搬回老家去住了,过年了嘛,根在老家不能忘本,这是杨刚说的。
他还说,乡音不改鬓毛衰,这话的意思是,当年自己爷爷在省城里教课那麽多年,入乡随俗固然是爲了适应生存,回到老家说话办事还是那个味儿,一点没有脱离群众的意思。
杨廷松脸上带笑看向自己的大儿子,这老大从家说话一如既往直来直去,从不把官面上的那种打太极的套路搬运回家,这一点颇得他的认可和欣赏:有本事在外面海阔天空,那是能耐、那叫玩意儿。
回到家里吃喝拉撒咱就普通人家,得会随遇而安。
杨刚认可父亲说的,他不反驳,他人过四十性情沉稳了许多,再不会像十五六岁那样玩生的、凭着年轻靠着狠劲跑出去闯荡。
参加工作二十多个年头,风风雨雨,迎来送往逢人说话办事又岂能不解这潜显道理。
正所谓一脉相连,他早就说过「一笔写不出俩杨来。」
所以,对自己的家人从不拿腔拿势。
然而他的这种镇服全场的气势并不是谁都佩服,起码他身边坐着的亲兄弟杨伟就从心里厌恶反感:就这也能当工商局局长?开国际玩笑了!
「小伟,我听说一中要进行改革,有没有这事儿?」
杨刚把酒杯放在桌上,「爸,你少喝点,我这一杯才见半儿,你这都喝完了。」
还别说,甭看杨廷松上了年纪,论喝酒杨刚还真不是父亲的对手。
杨刚有过总结,但凡是碰到两种人,他喝酒必醉:其一,喝酒不动地界儿、旁边预备一条手巾擦汗的;其二,喝酒小口小口抿的,你认爲一口闷了半杯,你就喝不过人家。
李萍接过话茬说道:「老大,今个儿妈就拍板儿让你爸喝了,要不是下午还得照看孩子,妈也得整一口。」
杨伟瞅了瞅大哥杨刚,有些不屑,心说你管的够宽,却笑着说:「提高教学质量而已,学校正商讨着明年开补课班的事儿。」
他今天没端酒杯,因爲下午还要讲课,这一点工作作风还是挺端严,而且身爲老师,他极其反感那些提溜着酒瓶子就往学校里走的同行,心说什麽玩意,喝酒背着人也就得了,大张旗鼓就跟别人不知道你喝酒似的,老师没有个老师的样儿,什麽玩意!
「后身儿那个厂子以前是一半一半,现在都归一中所有了吧!」杨刚随口念叨出来。
搞校办工厂,城区外的高中、初中或多或少都有,副业嘛,国家提倡干这个:「今年有不少下岗的,你们老师吃财政倒不至于,课余时间搞一搞三産很好嘛。」
也不知爲什麽,杨伟特别看不惯大哥的这种说话劲儿,心里正腻歪,柴灵秀那边说话了:「爸这上午可没闲着,熬鱼炖肉忙乎了半天呢,让他喝口解解馋!」
柴灵秀带着儿子过来时,公公正在给鱼刮着鳞片,她就把顔顔从婆婆手里接了过来,一直到大伯子两口子把自己男人接回家,侄子书文两口回来。
这才消停多会儿,所以这热闹日子说什麽也得喝点,这不,她拦着大伯子的驳回,自己也跟着端起了酒杯。
「妇女喝酒莫说临提!」
杨刚见兄弟媳妇儿拦道,挑起大拇哥幽默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