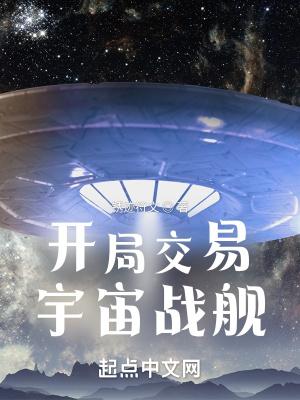爱上中文>穿越成为有钱人 > 第46章 追上(第2页)
第46章 追上(第2页)
差役走出几步远后,松了一口气,那青衫男子好大的气势,吓得他们反驳都忘记了!
这荣六郎书籍铺竟然卧虎藏龙,东家竟是这么不凡的人物!这样想着,腿脚也利索了,紧赶慢赶的就跑回县衙交差了。
程德青自那夜离府,一路坐船,沿着大运河北上,中间遇到几次查岗,差役听他口音是钱塘人士,盯着他主仆两个打量半天,二顺子心都提起来了,那差役挥挥手就让他们走了。
程德青暗想,那董如赞必是没有想到章修林把册子给了他,他自来湖南找曹大人了!
主仆两个连夜坐船,一路不敢多睡,就是困了也是轮流守着舱门。
这日终于到了乾州地界,根据官府的邸报,按照水运的行程,程德青算着时候,转运使曹大人这几日应在胡家塘驿站上岸落脚歇息。
主仆两个白日不敢露面,只夜里赶路,夜很深了,驿舍大门前亮着两只灯笼,上头显着“乾州府”
几个大字,起了夜风,灯笼晃来晃去,在地上投出一团昏黄的光晕。
就在这时,夜色下的驿道上,出现了一行四五骑的身影,那几人朝这边疾驰而来,卷出一阵清晰的马蹄声,很快,纵马到了近前,度减缓,几团黑色影子停在了门旁。
程德才正要走上前去看,驿站门洞大开,驿丞亲自领着婆子,殷勤的招呼那几个人进了驿舍。
驿站里热热闹闹一阵寒暄,驿站外,程德青和二顺子在门口徘徊了一阵,那看门的婆子终于伸出头来,轻蔑了看了一眼两人身上的布衣,鼻孔里出一声冷哼,就转回去“哐当”
的关上了门。
二顺子气恼,又轻轻敲了门,那老婆子开了门缝,漏出一双死鱼眼来,“何事?!半夜三更扰人清梦!此处是驿舍,可不是酒楼客栈!滚远些!”
二顺子忍了几下,程德青上前,掏出一锭足足十两的银子,对那婆子道,“最近的客栈也离此处十五里远,冬日也冷,只求阿婆通融一下,柴房坐一晚也是好的!”
那婆子眼睛睁得大些了,皮笑肉不笑的,“我见你们也不像是有官身的,更何况文书了,这驿站没有文书是不行的。”
说着又瞥了几眼程德青的袖笼。
程德青了然,笑着又掏出一锭二十两的银子递给婆子,这婆子才菊花绽开,一脸褶子的笑出来,“我可要说在头里,你们只能待在柴房,若是走动被大人查到,我可不会帮衬你们!”
二顺子也自然了些,忙接话道,“阿婆心善,我们怎么还能不识抬举,尽请放心!”
说着主仆两个就随着婆子进了柴房,那婆子鼻子哼着小调,手里摸着银锭子,一瘸一拐的又去了倒座房眯下了。
程德青和二顺子爬上柴房,眼见月亮在半空中照的驿站犹如白昼,两人便蹑手蹑脚的朝着单院望去,夜深安静,那单院一阵阵的说话声,想必就是刚入住的那伙人。
两人静静的蹲在屋顶,冬日寒冷,嘴边的雾气从鼻孔冒出来,二顺子渐渐觉得身上凉了,老这么趴着,非冻僵不可。他去瞧程德青,就见二爷眉头紧皱,似乎在凝神细听。
果然一会儿,门口又有一伙人进来住驿站。
一人走在前面,穿着劲装,身量颀长,突然就朝他们这边望过来。二顺子吓得赶忙伏在瓦上,程德青也压低身子遮住自己。
那群人住进了旁边的单院子,驿丞领着婆子小厮送茶送水,忙活了一阵,二顺子都冻得抖了,那院子才静下来。
两人正要从屋顶下来,后来的那伙人竟出了院子,直奔另一个院子去了。
这下院子里又喧嚣了起来。
宋祁朝曹大人行晚辈礼,曹录侧身避了,笑道,“世子客气,我怎敢受了都指挥使的礼,世子真是折煞我了。”
说着指着凳子邀请宋祁坐了。
曹录道,“世子从上京城而来,这是去往何处?在这寂静长夜,你我他乡偶遇也是缘分,倒是要喝一杯才好。”
宋祁沉声道,“我去适安府寻一故人,刚到驿舍,那驿丞说曹大人也驻扎在此,想必大人下一站也是适安府了,晚辈叨扰了”
。
曹录道,“正是,马上年关了,今年巡查最后一站就是那适安府,你我正好同行,也解了路途寂寞了。”
小厮端了酒菜,婆子温了酒,两人这就推杯换盏,论起时事来。
酒过三巡,曹录叹了口气,“哎,皇上沉迷画术,如今朝政被严阁老把持,左大人式微,太子年幼,我辈当如何?!”
宋祁两眼精光四射,毫无醉意,他拍了拍曹录肩膀,“大人勿忧,天佑我大启,必不会让奸人毒害百姓!祸乱朝纲!”
曹录喝的酩酊大醉,宋祁唤了小厮扶曹录上床歇息了,这才从院中走出来。
![入殓师[无限]](/img/1006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