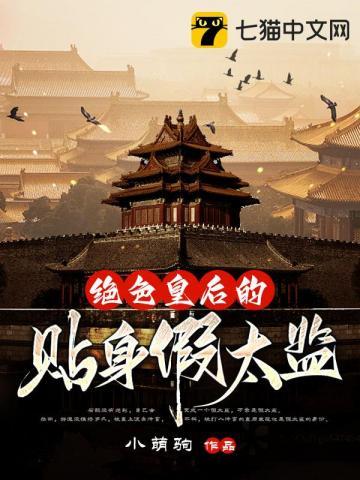爱上中文>长陵电视剧 > 第37章 第三十七章 金陵(第1页)
第37章 第三十七章 金陵(第1页)
“公子这次心脉确实受了重挫,好在有人及时替你疏通了督脉,接下来得静心调养一段时日,不可大意”
肖长老将叶麒心俞血上的银针缓缓抽出,又扎入了督俞血上,“可惜任脉未通,要不然老夫还能试试以任督二脉为契疏通阳维脉”
叶麒打了个喷嚏。这三月的武陵山还残留着冬日的料峭,风一丝一丝的渗过门缝,时有时无的拂过他赤、裸、裸的膀子,饶是这床榻边摆了一排炭炉子,后背还是激出了鸡皮疙瘩“还以为这回又捡回了一条命,听您老这话意,我还是活不久了”
“公子这淤滞之症毕竟是先天宿疾虽说你年少遇到了肯传功助你通脉的高人,可这股内劲实在霸道至极,这十一年来,纵使有人肯心甘情愿渡送功力,也无法与之融汇”
肖尹将针一根根取下,哑着嗓子问“这回为你运功疗伤之人究竟是谁此人既可疏你督脉,说不定也有可能”
“这就别想了。”
叶麒匆匆套上了衣裳,一边系衣带一边下了床踱到桌边,拎起茶壶对嘴灌了几口热水,“您就照直说吧,我现在这么个情况,还能活多久”
“往好处想,一年半载是没有妨碍了,若是在此期间能寻到此内功的修行之法,自可再往下多延数年”
肖尹也站起身来,“当然,这天下之大,也并非没有起死回骸的杏林圣手,假若公子有缘”
“行了长老,您身为灵宝阁阁主,东夏第一圣手,车轱辘话年年说,听的人只会觉得更绝望好吧”
叶麒手心搓揉着手心,难得揉出了点温意,“一年半载已是赚大了,我很知足。倒是您,眼睛怎么老眯着,是不是毒还没解清”
“瞎了大半个月,见光还是有些不适应,过些日子就好了终究是染过毒的,我上了岁数倒无妨,可惜了那些年轻的小辈,今后瞧远点的地方兴许就不如过去利索了”
肖尹低头叹了一口气,一抬眼,觉叶麒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离自己三丈远的位置,朝自己竖起了食指和中指,“长老,这是几”
肖尹“”
叶麒摊了摊手“远的嘛瞧不清就瞧不清呗,关键是走到跟前的人得擦亮了眼认清楚,东夏武林这次连头搭尾的跳到坑里去,人没给一锅端了已经客气了经了这事,以后八大门派谁还敢轻视灵宝阁,哼哼,您就不给药,让他们眯着眼闯江湖吧。”
肖尹摇头失笑“这次你将八大掌门救出水火,又斩去明月舟攻境的源头,眼下不仅是江湖人,就是百姓都对贺家军敬重有加,等回到金陵,皇上的勋赏是少不了了”
“勋赏”
叶麒一把推开房门,风卷着落梅,萧萧瑟瑟的拍打在衣裳上,“这次出门前,我还给陛下递了封遗书来着,也不知他看我这么全须全尾的回去,会不会有些惊喜呢”
人都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腥风战乱的年代,秦淮河畔都充斥那种霓裳一曲、水袖清扬的气质,何况是新朝盛年,光是穿过这一条十丈阔的建康街,几乎快被那一摞摞的千奇百怪闪花了眼。
这是指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长陵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年少没赶上好时候,所到之处不是孤村清苦,就是黄昏血染沙,南方富庶之地还真没怎么走动,倒是去过长安就是当时尽顾着攻打皇宫了,一直没来得及去街上晃晃。
“金陵城的花哨玩意儿还真是不少”
马车的窗轩敞着,长陵支着腮靠在上边,目光正好落在前方的绣楼上,但见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子凭栏而站,楼下围着一大群男人,正跃跃欲试的仰着头,不知在瞅个啥劲,“那是做什么”
符宴归本来在看书,闻言抬头瞥了一眼,“是福威镖局傅镖头的女儿,抛绣选婿。”
“哦,我知道,就是那种”
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那个红衣女子举起一个铜盆,用力甩出一枚红彤彤着光的火球来刹那间,底下的男人纷纷飞身跃起,个个皆徒手去抢,窜的最高的青年刚一触着,就被火球灼的嗷嗷叫,忍了忍没忍下去,往后一掷,一拨人又争先恐后的夺了起来。
马车匆匆而过,绣楼下的傻大个们一边惨叫一边拼命,长陵食指一抬,“你刚说抛什么来着”
“绣球。一般也就是带刺或开刃的刀球,烧成炭的确实少见,”
符宴归见怪不怪的翻了一页书,“傅镖头择婿的门槛是高了些,两个月也扔过一次,可惜接着的那位公子双手废了。”
“”
符宴归见长陵一脸的无言语对,不由一笑,“换作是你呢”
“什么”
“抛绣球,选什么球”
“我不会抛。”
“喔”
长陵没接茬,心中默默嘟囔一句要是一个不小心把人全砸死了就不好收场了。
符宴归没等着后话,复又低头翻书“你是不是奇怪那些人为何愿意去接那种绣球”
长陵“喔,是有些奇怪。”
“福威镖局乃是皇镖,若是能当上傅家的乘龙快婿,自是前景可观”
符宴归平平淡淡道“从傅家小姐的角度来说,若是最后真有人能徒手接住火球的,不正说明了对方的内功和身法皆是上佳么”
好像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扯淡。
就是长陵对于南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风雅闲适、吟咏诗书之上,才一进城就看了这么一出,实在有些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街头巷尾处处可见逞勇好斗之辈,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皆混迹于这繁闹之中,短短十一年,世道彻头彻尾换了一身装扮,认不出了。
大抵只有她还停留在过去。
恍若隔世的念头一起,长陵顿时失了兴致,符宴归见她靠回软垫,不由一怔“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