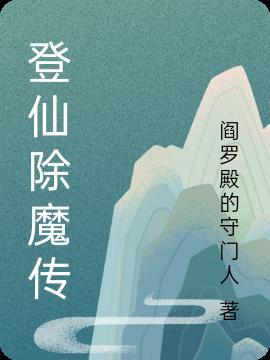爱上中文>结局好吗 > 17镣铐(第3页)
17镣铐(第3页)
棣棠先前是不准进寝阁的,只有梁潇开口,她才能进来。
二女一眼见到姜姮腕上的镣铐,神色大变,却终究讷讷不敢言语,屈膝恭送梁潇离去,才心疼地飞奔到床边去看姜姮。
子时,夜已过半。
梁潇沐浴后换了身天水碧的家常缎袍,拐去自己幼时住过的偏院,黑漆漆的,却有二十几个暗卫驻守,见梁潇过来,为的进屋扭动书柜后的机关,两面墙簌簌后移,闪出一条暗道来。
暗卫执一盏风灯,先进去照明。
梁潇拾阶而下,走了一段,面前有面宽几丈的墙,纵横交错的几道铁铸镣铐,捆锁着一个人。
不光是要锁着人,还得蒙上眼,周围悄静无声,兼之失去光明,过得久了,连时辰几何都不知,只有杳长死寂点滴细密的磋磨。
才不过半日,姜墨辞已经快要疯了。
他听到脚步声,忙问“谁”
半日水米未进,声音已有些嘶哑。
梁潇终究还是对谢晋下不了手,把他另外关起来,只拿姜墨辞开刀。
来回踱了几步,梁潇就是不出声,目光冷冷看着姜墨辞,蓦得,开口道“我实在想不通,你在成州的日子虽说过得不甚富足,但好歹顶着靖穆王内兄的名号,没有人敢为难你。为什么还要勾结乱党你真觉得自己七年前躲过一劫,后面就会一直好运”
姜墨辞反应了一阵,争辩“我没有勾结乱党,我只是救了几个无辜的孩子。”
“那几个孩子是乱党之后。”
“那不是乱党,是被抢夺田地,失去活路的平民。”
“不管因为什么,只要他们竖起旗帜反叛朝廷,他们就是乱党。”
姜墨辞无言,半天才道“你是辅政王。”
梁潇不屑“那又如何”
“你权势滔天,耳聪目明,焉能不知天下苦暴政久矣。豪绅权贵肆无忌惮圈占土地,恩荫制大盛,更戍法百年,底层读书人没有出头日,百姓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戍边士卒被层层盘剥。朝中大臣却只知粉饰太平,凡力主新政的有识之士早在七年前就被杀光了”
七年前,卫王和辰羡便是新政党之。
这就是姜姮一直苦苦追寻,辰羡不惜赔上性命也要做的事情。
梁潇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已是湛凉一片“是呀,已经被杀光了,七年前他们活着尚且做不成的事,如今,你还在做什么梦”
姜墨辞沉默良久,道“辰景,我记得,在最初,你并不是这么冷血残忍的人。”
梁潇讥讽道“我不冷血不残忍的时候,我得到了什么七年前,我同情过新政党,也帮过他们,可当他们的密谋东窗事,那些人为了保全辰羡,竟设计把我推出去替他顶罪。若非当时崔皇后救我,我早就已经死在大理寺的天牢里了。”
姜墨辞面露诧异“什么”
梁潇深吸了口气,提及往事令他烦躁生厌,不想与再与姜墨辞多言,转身要走,谁知姜墨辞听见脚步声渐远,忙叫住了他。
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把我关在这里,使这样的手段折磨人你有没有用同样的手段折磨过姮姮”
地牢暗不见天日,有一股涔涔寒气从地砖的缝隙往上泛,顺着袍裾衣角钻进去。
一阵令人绝望的寂静,不言而喻。
姜墨辞颤声道“为什么她做错了什么”
这话好生熟悉,好似谢晋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梁潇本来想让姜姮好好睡一觉,却叫姜墨辞又勾出几分绵密入骨的怨恨,出了暗室,又回到后院。
姜姮正在沐浴,双手连同镣铐搭在珉石台上,热水唤醒了沉睡的身体,她正哑着嗓子吃痛“咝咝咝”
。
梁潇甩开帘子阔步进来,把她从水中捞起来,捏着她的下颌,冷声质问“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很无辜七年前,是你自己说要用自己换父兄一条生路的,我救了他们,你又给了我什么”
“整整七年,你爱过我吗你给我的只是一具空壳,一具空壳值姜家父子的两条命吗”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