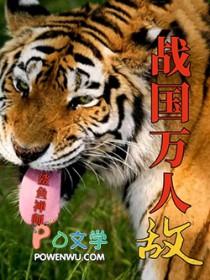爱上中文>我见公主多妖娆作者花惜言 > 第六章 花颜判(第3页)
第六章 花颜判(第3页)
“这次的钱二芦案就是,那贼子进了洛州界,刚放出‘白衣大仙’的名号,就被我堂妹盯上。否则此案也不会这么快被揭开。”
“当真?”
秦主恩兴更浓了,“不知令堂妹是如何现蛛丝马迹?又是如何揭开此案?”
“这……”
严愉面上作难,旋即又是一叹,“我这堂妹自幼丧母,缺乏教导。说得好听,是不怕不怕。说不好听的,就是狂妄自大,不信鬼神。对这种借鬼神巫术行骗的案子自然格外警惕。所以那钱二芦一到洛州刚把名声打出去,就引起严恬……就是我那堂妹的警觉。
“至于如何捉了他个现行……”
严愉支支吾吾,半方道,“说来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招数。
“严恬寻了个……妓女,扮成求子的民妇,面上十分虔诚,并极力奉承那钱二芦。因那妓女长得美艳,又穿金戴银,钱二芦反对其他前来求子的妇人不大上心,只一味想把这妓女先搞上手。
“后面的事情……咳,自然就,水道渠成……从钱二芦处搜出数斤迷香,又有那妓女的证词,人赃俱获……”
“你这堂妹竟然有这等本事?”
秦主恩击节赞叹道。
严愉却会错了意,忍不住老脸一红:“咳,咳……可不是!一个姑娘家,又是和妓女有牵扯,又是卷进这种风化案子中……唉,我那三叔宠女无度,就这么放任她不管。说来真是惭愧……”
“诶,严愉你这可就说错了!”
没等严愉自省完,秦主恩便神情严肃打断他,“世人对女子莫不苛责太过。平常女子倒还罢了,不过是中规中矩安时守份过完一生。
“可有那胸怀沟壑眼放下的奇女子,却因这等狗屁不通的世俗规矩固步封行,浪费了大好才能。更有甚者,被世俗不容,受那等庸人蠢货的污陷抵毁,竟毁人一生,实属可恶……”
“哟!听你这话,我倒成了‘那等庸人蠢货’了。”
严愉不怒反笑,心下明白他是因家中遭遇,又为他娘襄宁公主鸣不平,方才有此惊世骇俗之言。因而也不与他计较,继续道,“不管我这大堂妹是‘胸怀沟壑’也好,‘眼放下’也罢,反正这些年被我三叔纵得是无法无,且名声在外。
“一个姑娘家竟被洛州府的老百姓送了个混号,叫什么‘花颜(严)判’。我娘为这事儿成日介忧心上火,饭都吃不下。
“我们家你也知道。我娘就生了我和大哥两个,可毕竟还有个九岁的庶妹严惜呢。再有我二叔家庶出的严怡。”
说着严愉瞥了秦主恩一眼,“最是紧迫,今年已经十四到了花期,正是婚配的时候。若是严恬这名声不减反盛,洛州本就离京城不远,再传进京去,可不影响了其他妹妹的婚姻?”
“‘花颜判’?”
秦主恩眼睛一亮,“能得这名号,说明令堂妹不仅能断善判,相貌上怕也十分出众,所以才能以花做比。”
这厮!严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合着我说了半,你就只记住这一句?我那二堂妹严怡已经被你迷得五迷三道。你可千万别再招惹了这一位!离我们家的女孩儿远些!小心我祖父拿鞭子抽你!”
“良心!”
秦主恩一听这话立刻鬼叫起来,“你那位二堂妹我可从未招惹。我虽然偶尔逛个花楼,可还不算太混账。良家女子从不沾染,名门闺秀更是敬而远之。
“也就是那次去候府寻你,偶遇你那二堂妹,谁知她怎么就看上我了。我现在可是一见她就绕道儿走。”
“嗨!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是我们家人上赶着你似的。你瞅你这一脸邋遢胡子,知道的,我比你大半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比我大十岁!我二叔看着都比你年轻!严怡也也不知怎么想的,真是猪油蒙了心……”
“我觉的也是。”
秦主恩诚恳表示赞同。随后眼珠一转,突然有了个主意。
“诶,我说严二少。”
他边说边哥儿俩好搂住严愉的肩膀。
“既然你有正事,又嫌我磨蹭,不如咱俩就此分开各走各的如何?你快马加鞭向北去淮峰老家祭祖。我带着三寿一路逍遥自在慢慢西行。咱们最后在洛州府汇合。我不拖你后腿,你也不聒嗓催我。你看如何?”
“这……”
严愉看着秦主恩,眯起眼睛。这货不会又憋着什么坏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