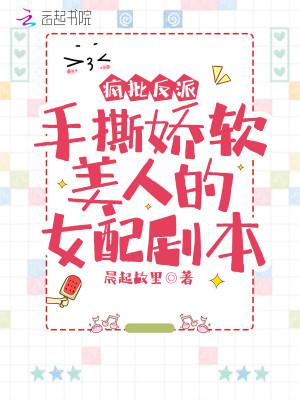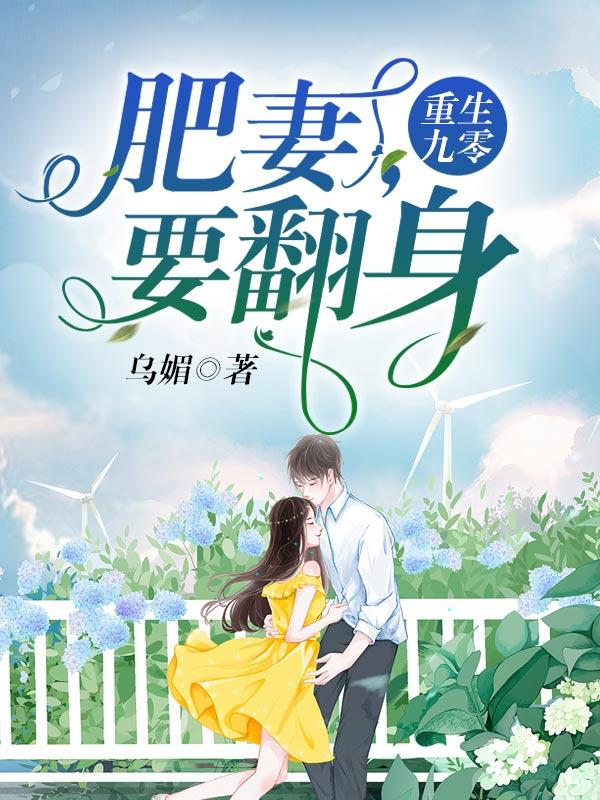爱上中文>掟上今日子的备忘录婚姻届 > 3(第3页)
3(第3页)
也不奇怪,可是在绝大多数的诈骗案例之中,不但被害人身上找不到什么问题,加害人的手法也不见得特别高明。
必定是因为被害人,还有加害人,都陷入了某种类型化的公式里。
不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而是因为有过二,才会无三不成礼。
“被害人之所以一直是被害人的循环自不待言,也有被害人成为加害人这种令人不想面对的循环。而且,这种事其实很容易发生。”
“是啊。”
我点点头,表达对围井小姐意见的赞同。
名侦探坐镇的推理小说里描写的凶手,也常会在最后一幕吐露悲惨的动机,声泪俱下地诉说凶手其实也是被害人。可能是因为作者与读者都下意识地认为“动手杀人一定要有能与其严重性匹敌的理由”
吧。
但与其说是痛快的复仇剧,这种转换被害人成为加害人的戏码只是种悲剧的结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不是我说,根本称不上痛快,只会留下痛楚,甚至是不快感。一想到现实社会一再重演着同样的悲剧,甚至已经超越了悲剧的范畴,应该要说是喜剧了。
“就
某个角度来说,虽然我因为自己一直受怀疑被误会,甚至总是以被害人自居,但同时也感到不安,生怕自己什么时候会变成加害人。”
“……既然都要被冤枉,干脆真的做些坏事,是这种思维吗?”
“我倒没想过这么疯狂的事……不过,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我的人通常都不是坏人,反而多是善良的老百姓。正因为善良,才会急着纠举犯人和坏人的不是,基于一股正义感想把我绞首示众——”
于法而言,明明没有证据,还误会某人是犯人,根本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
既然是犯罪行为,就不能说他们纯粹只是善良——只不过,这些人绝不是出于恶意地攻击我,至少不单是出于恶意——还出于道德观及正义感。
“——因此,我也担心自己可能正不知不觉地做着同样的事。对报道及新闻囫囵吞枣,没有理由,也没有根据地认定谁是某件事的犯人。”
“在我这以报道为业的人听来,还真是逆耳之言呢。”
围井小姐的唇畔浮现一抹笑意。
“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犯那种错误,所以本次才会想制作这样的专题,但的确,由于近年新闻媒体的竞争实在太过激烈,因此产生了许多的冤罪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的回答似乎被她以为是在讽刺什么,但如果只将这种现象单纯视为犯罪报道的一体两面,反倒可能会完全忽略了本质。
不只是以报道
为业的人,大家都做着同样的事。在家里、在学校、在公司,大家都做着同样的事。真要说的话,“找犯人”
和“猜犯人”
根本不是什么两面,只是人类真实的一面。
当然,虽说影响力有大有小,现在这个时代,即使是个人也能向全世界发表意见及偏见。
不,推给时代也很奇怪。
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流传的谣言,结果却造成国家灭亡或大恐慌的逸话早就不胜枚举。这也是在历史上重复到令人厌烦的一种发展类型。
“话题有点偏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么,隐馆先生,如果不想被一再冤枉,难道只能保持‘从来不被怀疑’吗?”
“若是如此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单纯要应付被人冤枉后的窘境已经不容易,还要在从未有任何经验时未雨绸缪,简直……反过来说,如果最好的对策真的是‘从来不被怀疑’,那么不就等于是在说‘只要被怀疑过一次,就可能再也难以翻身’了吗?”
这么想的话,或许我还算幸运,因为也有人只是蒙上一次不白之冤,就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整个人生都毁掉了。
别说是有二就有三,光卷入一次的冤案,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机会,一次就失去了一切。
于是为了不被怀疑,平时广结善缘便显得相当重要。正因如此,若能像信用合作社的冒领犯那样,与周围建立起“即使已经罪证确凿仍会被信
任”
的关系,真有个遭遇麻烦的时候,还是会有可靠的伙伴在身旁。
以我为例,绀藤先生正是如此。
在出版社打工时发生的案子,大家都怀疑我,只有那个人,直到最后都相信我。
我很高兴,同时也感到胆怯。
觉得仿佛是坏心眼的我正在利用他的善良——虽说这样想也真是把自己贬得太低,但是人一再地被怀疑,结果就是会把自己贬得这么低。
“只是,虽然我们会认为平常就行得正、坐得端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也有人就是达不到‘平常’的标准。”
怎样都无法好好过日子,跟不上时代,与周围的人也处不好。去批评这种人“谁叫你平常不好好做人”
,未免也太残酷了。
事实上,也有人纵使成天做旁门左道的事也没事。
更何况也没有人能保证平常行得正、坐得端,就绝对不会成为冤罪事件的被害人。
虽不完全适用于信用合作社的冒领犯,但如同在推理小说中“最不可疑的登场人物就是真凶”
俨然成为一种公式,“没想到那个人会做出这种事”
这句话背后的意义,与说出“果然是他啊”
所伴随的恍然大悟,或许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无论是谁,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避免卷入冤案。
“这跟不管是成绩斐然还是素行不良,不管是受欢迎还是被排挤,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班上霸凌对象的情况其实大同小异——要成为身陷冤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