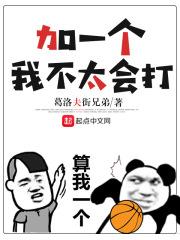爱上中文>当我救了江湖公敌 > 第23章(第2页)
第23章(第2页)
身体越是劳累,脑袋越是清醒。
容清樾半靠美人榻,美眸半睁半闭,榻前的熏香往上升起缥缈轻烟,清甜的梨香并不腻人。
姑姑从不是宽厚的人,但暗里与小辈如此计较倒是头一回儿。
小六真如那妇人所言,强抢民男,丧尽天良而无人敢告无人知,可见现今的云都已是隐藏在平静湖面下的深渊。
北晋、西佑、南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能在现世自保。
两日后,晨光将突破天际的时刻,房门‘笃笃’作响。
容清樾睁眼起身,随意捞起旁边搭着的薄披风,喊到:“进。”
梁郝和子厦通红着双眼,合掌对容清樾拜一礼:“殿下晨安。”
“查到些什么?”
容清樾接了侍女递来漱口的茶水,含了放在口中,除去嘴里难闻的气味。
“那妇人的丈夫的确是体无完肤地送回了村子,村里人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六公主所为。”
梁郝将这几日查访得来的消息禀报给她,“不过他们村里的人不信这妇人会为丈夫讨公道。”
容清樾抬眼。
“妇人姓赵,名立笑,她的丈夫高见志乃青木村里出了名的好皮相。年少成婚,但因高见志貌美,赵娘子貌平凡,怕丈夫美名在外,便每隔几日就找理由打骂高见志。高见志虽没有太高的心气,但脸肿着终是不敢出门见人。”
梁郝继续说,“唯一一次得赵娘子允许出门,还被六公主带走,落了个短命的下场。”
他们俩花了好些银子才从村民口里套出话来,听了故事,啧啧称其,只道这世间没有这么悲惨、懦弱的男子了。
“有村民说,赵娘子只有在丈夫被送回去的时候哭得悲恸,口喊丈夫死的冤枉要去报官。一日后见了个戴斗笠的男子,接了一袋银子,改口对外称高见志是在家中突发急病暴毙而亡。”
容清樾手中的簪子一搭没一搭的敲着铺了锦布的桌子,闷响。
那日山中,赵立笑哭得梨花带雨,好不伤情,也不知那‘情’字带了几分,‘利’字又带了几分。
她哼笑:“这世间,人人都是可以上戏台子的料。”
梁郝说完,子厦跟着接上:“高见志确实是从六公主府抬出,有明阳街的小喽啰可以作证。那妇人,除去她与丈夫之间感情,以及并未前去衙门状告,其余都为真言。”
簪子停在桌角,硬生生磕弯了,容清樾冷声问:“赵立笑口述的,许多男子都被小六带走,也为真?”
“是。”
容清樾‘蹭’地起身,气得肺疼,兀自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却没有发泄的途径。
子厦嘴笨,对云都的人和事都不熟,嘴张了好几次也没说出什么安慰人的话来,梁郝牵强扯出一抹笑:“殿下,六公主性子跋扈恶劣乃人人皆知的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