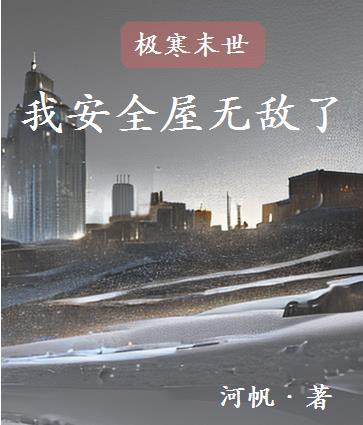爱上中文>炎暑将至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倪殊抬眉,“可是这张脸看起来人畜无害,t就是个婴孩,若不是角和蹄子,是很能迷惑人心的。”
“邹关强的意思是,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不会被恶魔的外表迷惑。”
她一顿,望向倪殊,“你说他画的这个婴孩是谁?”
倪殊想了想,“许院长刚才说邹关强有一个女儿,但我想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恶魔,所以这幅画应该只是一个隐喻。”
“我认同,”
辛夏抿嘴笑笑,却显得有气无力,“不过或许他也没有想到,这幅画会变成一个预言。”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猜想,邹关强的女儿应该就是梁大成的儿媳,邹莹。”
倪殊的眉头倏地皱紧,“辛夏,你在怀疑什么?”
“说不清楚,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辛夏心里很乱,随便敷衍了一句便机械地继续顺着楼梯朝下走。倪殊跟在后头,看到她走到楼洞,背影嵌入一片斑白的世界时,提高声音问了一句,“怪在哪里?”
辛夏回头看他,刚想说些什么,忽然听到一阵门栓拉动的声音,刺耳又急躁,紧接着,余光瞥到侧面墙上一扇不起眼的小门被从外面打开。
羽毛般的雪片被风卷着扑进来,门外面是她熟悉的景色,虽然那些砖墙灰瓦已经被大雪笼住,变得有些模糊。
她心里一怔:这扇门为什么开了?她本来以为,它只是一条应急通道。可还未来得及细想,忽然听到短促的剎车声,一辆面包车缓缓闯进眼帘,横在门外。
车窗摇下,里面的人探出脑袋,冲门外那个拿着门锁的人抱怨,“我发现真是巧了,但凡变天,你们这里就死人,次次都得我风雨无阻地往这儿跑,这个月都第几次了?”
拿着门锁的人赔笑,“您多担待,咱们这地儿不比别处,别的医院人去了都是求生,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求死。许院长说了,改天请哥儿几个吃涮肉去。”
说话间,主楼右边,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走出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只担架。担架很沉,两人的步子在湿滑的雪地上踉跄起来,有点稳不住。拿锁的那人忙走过去帮忙,扶住担架一侧,朝上面那个鼓鼓囊囊的蓝色裹尸袋看了一眼,嫌弃地别过脑袋,“这么胖。”
“这还瘦了呢,刚进来的时候两百多斤呢,每次打针都得个人才能按得住。”
“怎么死的?”
“血脂太高,又骗不了他吃药,他精得很呢,鼻子比狗还灵,哪怕饭菜里放了一点点药粉,他都不吃一口,这下好了,堵了血管见阎王了,也算如愿以偿。”
三个人快步走到面包车后侧,把担架抬进早已打开的车厢中,其中一人随车,另外两人则走进小门,把铁门重新拴好。
面包车呜鸣着走远,辛夏却依然站在原地没动,雪落在裹尸袋上的沙沙声仿佛还潜伏在耳边,准备随时冲出来在她脆弱的神经上咬上一口。她的头发被雪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花碰上头皮,化成一绺绺冰凉的水珠,顺着发丝流下,滴入脖颈。
辛夏狠狠打了个寒战。
“冷啊?”
倪殊搓着手走到辛夏旁边,他忽然生出一种错觉,身旁的女孩脆弱得仿佛能被一片雪花击溃,“找点热乎的吃吧,天寒地冻的。”
“涮羊肉如何?”
辛夏扭头看他,“刚才听他们说这附近有家涮肉很好吃。”
倪殊比了个ok的手势。
白烟从铜锅里袅袅升起,覆住倪殊的镜片,他取下眼镜擦拭,抬起头来时,看到辛夏正起身端着盘子朝锅里下肉卷。她刚才脱了大衣,只着一件高领黑色羊毛衫,不算贴身的设计,却被她玲珑有致的身材衬托得高低错落,引人遐想。
不过倪殊现在没有时间做此毫无意义的肖想,他看着锅子里鲜红的肉卷被沸腾的清汤滚熟,胸口忽然有些堵。
“刚才那车是殡仪馆的吧”
“倪总,咱们能不能先好好吃完一顿饭再讨论这个话题。”
辛夏开始搅拌自己面前的小料,把一碗麻酱韭菜花和腐乳酱调得五颜六色。
倪殊笑笑,这才发觉辛夏的指尖白中透着点青,显然已经耗尽了能量。他把旁边一盘肉下进锅子,看着它们在沸水中挣扎起伏,不动声色地扬了扬眉峰。
自首
一顿饭吃得尽兴与否,饭搭子很重要。
倪殊觉得辛夏是一个很不错的饭搭子:她不挑食,吃嘛嘛香,而且吃相也很好,挟菜舒缓,快而不急,干净爽利。
一桌子荤馔素食被两人快速解决掉,铜锅下炭火将熄,冒出零星几点红光。
倪殊撂了筷子叫服务员结账,一边扫二维码一边冲辛夏道,“饭我请,故事该你讲了吧。”
辛夏争不过他,只能悻悻地去拿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没有证据支撑的事情倪总也乐意听吗?”
倪殊抿唇,“怪不得不开心,原来又遇到一件只能心证的案子啊。”
辛夏被人猜破心事,咬着牙没说话,先他一步走出饭馆。
雪片从头顶灌下来,在人世间织成一张繁乱又面目模糊的大网。辛夏看着不远处那幢梁家三代人栖居的,仿佛被缠绕在迷雾中的六层小楼,心里忽然涌上一股巨大的悲凉,压得她透不过气。
她走下店前的台阶,冲跟上来的倪殊轻声道,“我总觉得安雅一直没有走,自那晚后,她就留在了梁家,变成了梁家的第六个人。”
倪殊“啊”
一声,一只手搓搓胳膊,“讲故事归讲故事,别整玄学这一套,听着怪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