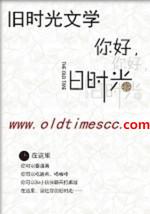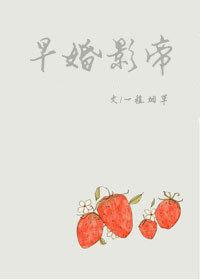爱上中文>李廌师友谈记 >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第1页)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第1页)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温儒敏的现代文学自选集《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题记“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这是鲁迅在论文《摩罗诗力说》结尾说的一句话。鲁迅于1907年写下这篇鼓吹浪漫主义反抗之声的檄文,时年26岁,还是个热血青年。怀抱“新生”
理想的鲁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觉之声”
,来破“中国之萧条”
。记得四十年前,我还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
而感奋,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
之宏愿。40年过去,我要给自己这个论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这是怀旧,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
四十年来,我出版了20多种书,发表200多篇文章。说实在的,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得出手”
的不多。现在要出个自选集,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2021年4月《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研讨会合影
顾与检讨——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某些斑驳光影。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只是我专著之外的部分论文,也有若干是在专著出版之前就单独发表过的,东挑西选,汇集一起,得55篇。论集分为四辑:鲁迅研究、作家作品论、文学思潮与批评研究,以及学科史研究。大致就是我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当然,我还关注过语文教育等领域,那些论文已经另有结集出版。
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是从鲁迅开始的。1978年考研究生,找本书都不容易,但鲁迅还是读过一些,就写了一篇谈《伤逝》的文章(记得还有一篇关于刘心武的),寄给了导师王瑶先生。后来到镜春园86号见王瑶先生,心里忐忑,想听听他的意见,老人家却轻描淡写地说文字尚好,学术却“还未曾入门”
。大概因为缺少资料,探讨的所谓观点,其实许多论文早就提出过了。尽管如此,我对鲁迅研究还是一往情深,在研究生期间花费许多精力在这个领域。收在集中的谈论《怀旧》《狂人日记》和《药》的几篇,以及《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都是研究生期间的产品。后者是硕士论文,题目有点偏,想弄清鲁迅为何喜欢日本理论家厨川白村,当时这还是少有人涉足的题目。后来又断断续续在鲁迅研究方面写过一些文字。20世纪80年代受“理论热”
的影响,一度还挺热心去“深挖”
鲁迅作品的意蕴,做“出新”
的解读。比如对《狂人日记》反讽结构的分析,对《伤逝》“缝隙”
的发现,对《肥皂》的心理分析,等等,都带有当时所谓“细读”
的特点。但我更关心的还是鲁迅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1990年代以后,学界对鲁迅的阐释注重脱去“神化”
,回归“人间”
,多关注鲁迅作为凡人的生活一面。这也是必然的。然而鲁迅之所以为鲁迅,还在于其超越凡庸。我这时期写的几篇论文,格外留意鲁迅对当代精神建设的“观照”
,对当时那种轻率否定“五四”
和鲁迅“反传统”
意义的倾向进行批评。如《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
之预感》,都是紧扣当代“文化偏至”
的现象来谈的。始终把鲁迅视为“精神界之战士”
,看重其文化批判的功能,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
。
我研究的第二个领域,是作家作品,涉及面较广,也比较杂。不过收入文集的评论并不多,只有15篇,研究的大都是名家名作。其中郁达夫研究着手比较早。我在研究生期间,就编撰过一本《郁达夫年谱》。当时还没有出版郁达夫的文集,作品资料都要大海捞针一般从旧期刊中去收集,很不容易,但也锻炼了做学问的毅力。年谱有20多万字,王瑶先生还赐以序言,当时交给香港一出版社,给耽误了。收在集子中的几篇关于郁达夫的论述,因为“出道”
早,也曾引起过学界的注意。1990年代以后,我教过一门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的课,就一些名家名作进行评论,努力示范研究的方法,解决学生阅读中可能普遍会碰到的问题。收在集子中的《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
现象》和《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最初就是根据讲课稿整理成文的。后来还写过好几篇类似的作家论,又和人合作,出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被一些学校选做教材。我所从事的学科叫“现当代文学”
,名字有点别扭,现代和当代很难区分,应当打通。我主要研究现代,但也关注当代,写过不少当代的评论。比如贾平凹因为《废都》的出版正“遭难”
受批判那时,我并不赞同对《废都》进行简单的否定,认为《废都》在揭示当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是有独到眼光的,甚至提出二十年后再来看《废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苛求了。而当莫言获奖,大量评论蜂起赞扬,我也指出莫言的《蛙》在“艺术追求”
上的“缺失”
。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抱怨当代评论有两大毛病,一是圈子批评多,“真刀真枪”
的批评少;二是空洞的“意义”